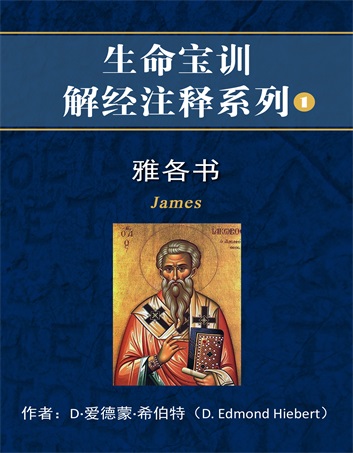八、以节制的果效来试验信心(3:1-18)
3:1-18 (1)你们中不应有许多人自以为是教师,我的弟兄们,因为你们知道我们这些教导的人将会受到更严格的审判。(2)我们都在许多事情上跌倒。若有人在他所说的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3)当我们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它们顺服,我们就能调动整个动物。(4)或者用船为例。尽管它们如此巨大,又被大风驱使,它们却被非常小的舵操纵,随着掌舵的意思而行。(5)同样,舌头是身体上的一个小器官,但它却说大话。想想看,一簇小小的火焰可以点燃一片巨大的森林。(6)舌头也是火焰,我们百体之中一个罪恶的世界。它败坏全身,点燃他生命的整个轨迹,并且它自己是被地狱之火点燃的。(7)各类的走兽、飞禽、爬行类,以及水族,本来都可以制伏,也已经被人制伏了;(8)但是没有人可以制伏舌头。它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致死的毒。(9)我们用舌头赞美我们的主和天父,也用它咒诅人,就是那照神的形象被造的。(10)从同一个口里出来颂赞和咒诅。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11)甜水和咸水可以从同一个泉源中流出吗?(12)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或者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13)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愿他通过他良好的生活,通过来自于智慧的谦卑行为显明出来。(14)但是如果你们心里怀着苦毒的嫉妒和自私的野心,就不可为它自夸,或者否认真理。(15)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不属灵的,属鬼魔的。(16)因为你们在何处有嫉妒和自私的野心,你们就在何处可以找到扰乱和各样的恶行。(17)但是从天而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热爱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和善果,不偏不倚,真诚无伪。(18)在和平中撒种的、使人和平之人,要获得义的丰收。
第3章是关于节制的一节,它讨论舌头的能力,以及如何控制它。第2节说,控制舌头的能力是“完全人”的标志,也是对活泼信心做进一步试验的关键。这个试验处理前面仅浅浅提及的一件重要事情(1:19、26,2:12)。圣经有多处论及良言或恶语之能力的经文,而雅各书这一章则是关于控制舌头的问题之经典解释。雅各坚持认为,活泼的信心必须通过有效控制舌头显出其生命力来。布卢说:“喉舌最终与心灵相连。令人喜爱的言语需要智慧之源。我们必须同时控制谈吐与培养思想。”[1]
雅各指出了控制舌头的意义(1-2节),生动地刻画了控制舌头的重要性(3-6节),断定人无力控制舌头(7-8节),谴责不受控制的舌头之自相矛盾(9-12节),并以如何智慧地控制舌头的讨论作为结束(13-18节)。
(一)控制舌头的重要性(1-2节)
在前一个试验中(2:14-26),雅各坚持认为活泼的信心必须用行为显明自己。第3章继续要求有产生行为的信心,但是所要求的有所不同。雅各坚持认为,活泼的信心同样必须生出内在节制的果子。而是否能够控制舌头,是检验节制的最佳手段。雅各同意耶稣的教导(太12:34-37),人的话语揭露了人的本性。作为说话的器官,人如何使用舌头可以轻易地暴露其内在本性,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太12:34)。说话的能力是神赐给人的最大恩赐之一;基督徒必须时刻谨守口舌,不可滥用这威力强大的恩赐。雅各首先讨论了基督徒教师应当控制舌头的问题(1节),然后扩展到一般的信徒身上(2节)。
1.教师的责任(1节)
鉴于教师的工作主要通过舌头来完成,因此对于基督徒教师来说,控制舌头极为重要。雅各完全意识到教师的责任,因此给予严肃的警告:你们当中不应有许多人自以为是教师,我的弟兄们,因为你们知道我们这些教导的人将会受到更严格的审判。这种“多少有点解释性的翻译”,避免了“这句话里雅各不鼓励人们做教师的印象”。[2]这句话并不是要攻击教师的职分或者教导的功能,因为雅各随即就承认自己也是一位教师。相反,他是希望阻止那些不够资格的人匆忙地教导他人。
在提出警告的时候,雅各将否定词(mē)放在了许多人(polloi)之前,并将这两个词放在了句首,表明有些人应当承担教师的职分,但是也有许多人不应当做教师。翻译为自以为是(ginesthe)的动词,其基本含义是“成为”,而动词的现在时态描述了一个持续不断的动作。带有否定词的祈使语气暗示,许多人以教师自居已经蔚为风气,但是这种趋势应当停下来。利利寻求表现出这句话里禁止的意思,于是将其翻译为“你们当中不要有许多人把自己高抬到教师的地位”。[3]教师这个词[4],在这封书信中仅见于此,并不仅限于正式认定的教师,也包括那些站起来指导同伴的人。在犹太人大流散后的会堂中,那些被认定为“教师”的人负责教导教义,对成员们进行道德训练。但是,显然这不是一个官方认定的群体,会堂中有许多成员会主动站出来,一起来承担这样的服侍。
这个禁令清楚地反映出早期基督徒聚会时的民主氛围。正如我们从哥林多前书14:26-34所见,几乎所有的信徒都可以在聚会时有所贡献。这种自由提供教导的方式,与此信读者熟知的犹太会堂所具有的自由风格相协调。在犹太会堂中,任何人都可以起来施教(参徒13:5、15)。另外,早期教会中的教导事工十分受人尊重。因其独特的性质,基督教赋予教导重要的地位(太28:19-20;徒13:1;弗4:11),并鼓励信徒成为教师(来5:12)。这种自由教导的风格,显然会让某些不够格的、不清楚教师责任的成员,自以为是地攫取成为教师的机会。他们贪图受人尊重的教师地位,却不愿付出担任教师所需要的代价(参提前1:7)。正如劳斯所说:“但凡重视教育、尊重教师的地方,无疑都会不断地出现这样的诱惑,让野心勃勃之人跃跃欲试。”[5]雅各所谴责的,正是这种注重教导的虚假狂热。他无意限制那些清楚知晓神的呼召、在聚会中教导他人的合格教师。
直接呼语我的弟兄们,标示这是书信中新的一段。[6]雅各以此说明,他接纳和承认自己所警告之人,认为他们是神家里地位相等的成员。这个呼语以同位语的形式担任第二人称复数动词的主语,清楚地表明“这里的问题不是要解除教导异端的教师职分”[7],或者防止假教师有机会推广不正确的教训。雅各所想的,是抑制某些激进的成员在说话时“滔滔不绝地轻率发言、使用虚浮的修辞、滥用语言、误导性地断言等危险”。[8]
因为你们知道我们这些教导的人将会受到更严格的审判,说明了警告的理由。因为你们知道(eidotes[9])译自一个表原因的分词,表示直接的因果关系,暗示那些被警告之人的确知道,想要做教师会让他们受到更严格的审判。与表示劝勉的动词联系在一起,这个分词也带有劝勉的味道;雅各希望他们不要忘记,作为教师他们“将会受到更严格的审判”。从第二人称的祈使语气转换到第一人称复数的我们这些教导的人,带有怀柔的意思,也显出作者的谦卑。作为教师,“他在给别人警告的同时,也不会忘记将警告应用在自己身上”。[10]“这是作者所暴露的仅有的个人信息。”[11]
将会受到更严格的审判(更字面的意思为“我们将接受更大的审判”),清楚地说明了教师们所要面临的情况。动词审判(krima)指的是法官所宣告的判决。这个词本身是中性的,但是在新约中它通常表示某种不利的判决(可12:40;路20:47;提前5:24)。动词的将来时展望了教师们将来站立在基督的审判台前(罗14:10-12;林前3:10-15;林后5:10),因他们对他人所造成的影响而受审的景况。“在末日到来时,所有的事工都要接受神的审查,经受严格的质询;神的认可而非世界的看法,才是真正的认可。”[12]更严格的(meizon krima,“更大的审判”),暗示他们匆忙地自承为教师,却没有忠实地履行教师的职责。神的审判所遵循的原则是:影响力越大,责任也越大;对他人造成更大影响的人,将会受到更严格的审判。比较级的形容词“更大的”,表示在审判台前被定罪的程度。那些担当神的信使之人,将会因他们的地位而受到更严格的审判。雅各深刻地洞悉基督徒担任教师任务的严肃性。正如佐德易阿特斯所说:
如果我们因为想要炫耀而去教导他人,在宣扬基督的时候却没有活出基督,将会受到神严厉的审判和定罪;但是,如果我们出于真诚的爱主,想要劝勉那些听我们教导的人,那么我们应当欢迎神的审判,因为那将意味着极大的奖励。[13]
2.完全人的证据(2节)
我们都在许多事情上跌倒,阐述了一个普遍的事实,加强了前面的警告。教师也不免于“我们都……跌倒”的事实。[14]都(hapantes)即“每个人”,是一个很强的形容词,而且雅各将其放在句末,给予更大的强调。这句话并不单单适用于教师,所有人都落入其中(王上8:46;箴20:9;传7:20;罗3:9、23;约壹1:8)。跌倒一词的用法和2:10一样,表示道德上的失足。在字面意思上,这个词表示有人被障碍物绊了一下,因此失去平衡或者跌倒;在象征意义上,它表示有人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犯下了可耻的错误,或者犯了罪。
伦斯基说,“跌倒”并不一定表示致命的过失,它指的是我们在前进的路途中有时不免犯下的错误。[15]动词的现在时态表示反复出现的行为,表明我们在生活中会重复经历各种跌倒。这一清醒的认识通过句首的polla一词凸显出来——它被译为在许多事情上。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修饰动词的副词,或可译为“因为我们各人常常都在跌倒”(罗瑟拉姆译本)[16]。但是,这个词更可能是形容词。它可能表示罪的数量,例如修订标准译本的翻译“许多过失”所暗示的,但是它更可能按照新国际译本所翻译的那样,表示各种各样的罪。按照这样的理解,它表示我们可能跌倒的各种各样的方式。正如埃普所说:“我们的舌头可以无数种方式让神的名蒙羞。它可以讲述一个下流的故事,它可以在急怒中说出亵渎的话,它可以传播无聊的谣言,它可以报告半真半假的谎言。”[17]因此,滥用舌头可能让人跌倒的危险,远远超过了教师因其教导事工而跌倒这一种情况。
通过“我们……都跌倒”的说法,雅各再次勇敢地将自己也包括在内。他自己的经验证实了人不免犯错的事实。伦斯基说:“这是雅各勇敢地认罪。”[18]但是,通过诚实地认罪,他赢得了继续说话的权利。他坚持认为,如此跌倒绝非一件无关紧要、可以轻轻揭过的事情。然而施蒂尔指出了雅各认罪的一个必要限制:“这并不是说他在圣灵带领下写出的这封信有任何错误,可以让他们或者我们来批评;他只是说,在日常生活中,当他所行之事与使徒职分无关时,甚至他也找不到一个在话语上没有任何过失的完全人。”[19]
对于基督徒而言,控制舌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它是基督徒品格的试验,是他们生命成熟、有节制的证明。若有人在他所说的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条件从句若有人在他所说的上没有过失(字面意思为“没有跌倒”),暗示某种现实状态;现在时态的动词表示他的生活已经不像普通人一样受到反复犯错的阻碍。“在他所说的上”(字面意思为“在话语上”),并不单指教导;它将一般的说话都包括在内。这里所指的不是无心的失言,而是指人经过深思熟虑所说出的话语。参考前一节的内容,读者不能认为这人处于一种完全无罪的状态下。
他就是完全人,简洁地评价了刚刚所描述的这人之特征。指示代词他(houtous,“这人”),对满足前述条件之人进行总结和归类。唯有这样的人,雅各才会称其为完全人(teleios anēr)。这里的人(anēr)并不单单指“男人”(参1:8、12、20)。但是盖布兰(Gaebelein)合宜地指出,这个词的确表明“雅各没有采纳当时常用的男性视角,认定滥用舌头主要是女人容易犯的过失”。[20]
“完全”并不表示这人全然无罪,达成了此生无法达成的目标(参3:2上)。正如1:4的用法一样,这个形容词描述了此人在属灵上趋于成熟,能够完全节制自己。他拥有“成熟的宗教生活,知识和品行圆熟丰富,就像一位与属灵的婴儿相比在基督里长成的人一样。”[21]
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将这种成熟进一步描述为能通过信心的试验。新国际译本未能译出的Kai这个词,连同“全身”一词,完全显明他控制舌头的能力所代表的意义。舌头是身体中最难控制的部分,因此能够控制舌头,就表示他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即控制自己的行为。他可以控制自己身体的各个部分及其能力,不让罪借此表达出来。勒住(chalinagōgēsai)这个生动的词汇,表示他可以制约自己的全身,不被罪利用,同时指引全身采取合适的行动。他能够掌管自己的整个身体,使之就像上了缰绳的马,可以随意指挥。在路加福音11:53-54里,耶稣是如此完全之人的完美榜样。另见彼得前书2:21-23。劳斯说得好,这种完全“并不与人持守更高的美德标准有关,而是指有人处在一种理想的整全状态下”。[22]
巴克利说:“雅各的意思绝不是沉默是金。他不是请求读者……胆怯地保持沉默,而是希望他们智慧地使用语言。”[23]雅各也没有提示说,人必须主动保持长期的静默,以修炼出掌控舌头的能力。有效地勒住、掌控舌头的能力,唯独来自内住的圣灵之大能。
(二)控制舌头的必要性(3-6节)
受控的舌头的重要性,显明了有效控制它的必要性。雅各生动地描述了控制舌头的重要性(3节-5节上),刻画了不受控制的舌头所造成的损害(5节下-6节)。
1.受控的舌头所达成的果效(3节-5节上)
雅各引用了读者熟悉的两个例子,说明合适的控制所带来的效果(3-4节),并将这两个示例应用到舌头上(5节上)。
(1)举例说明合宜地控制舌头(3-4节)
雅各引用了两个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例子,以说明我们需要合适的控制。
①马和嚼环(3节)
第2节中提到勒住舌头,自然地引出了马和嚼环的例子。当[24]我们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它们顺服,我们就能调动整个动物。当(ei de,字面意思为“如果现在”)这个词引出的第一类条件句,并不表示对条件的怀疑:日常经验表明,只要控制了关键之处,我们就能调动马匹,因此我们也同样可以有效地控制人类的舌头。新国际译本没有翻译的de(“现在”)是一个转换连词,引入进一步的讨论。
属格形式的马被作者强调性地提前,希望引起读者对控制马嘴与人嘴的相似之处的重视。原文中,“马”和“嚼环”前面的定冠词都是属格形式,仅仅代表各自的类型。复数的“马”暗示,若嚼环能够控制某一匹马,就可以适用于所有的马匹。实际上,佐德易阿特斯提出,这里的复数也许表示“雅各承认每匹马的个体差异性”,因此“对于各种不同的马,都有适合它们的嚼环”。他就此给出的应用是:“若神给某人带上的嚼环与其他人的有所不同,或者这嚼环造成的伤害比别人的略多一点,愿他不抱怨。”[25]
翻译为嚼环的单词可以指代整个缰辔,也可以单指放在马嘴里的那一小部分。参照第2节,最好这里也同样翻译为缰辔,因为整个系统需要协同工作,才能让嚼环控制住马匹。动词放(ballomen)或者意为“投掷”,是一个温和的单词,没有暴力强迫的意思。其现在时形态表示反复发生的动作,说明这是一种常规的做法,总是可以得到预想的结果。施蒂尔说,因此,可以控制“强壮高贵的马匹”,是“人可以利用动物的特点让所有动物服役的象征,因为不是我们力大使其屈服,而是我们明白如何在正确的位置使用合适的工具来控制它们”。[26]
叫它们顺服,表明使用缰辔的目的是让马匹全然顺服,并不仅仅是为了管辖它的嘴。但这一成就并不是偶然实现的。由缰辔所代表的控制机制,必须被用在合适的地方。(谁会把控制马匹的缰辔放在它的尾巴下面呢?)所以雅各感兴趣的并不仅仅是“驯服的舌头”,而是通过合适地控制舌头,显明人生命的各个方面都应受到控制。
我们就能调动整个动物,说明了作者业已暗示的结果。动词调动(metagomen)的意思是改变方向,在新约中仅见于此处和第4节。它的现在时形式表示反复的动作,说明这是一种习以为常的结果。原文中的kai(“和”,“并且”;新国际译本未译出),补充了控制马的嘴就可以调动整个动物的事实。这两个动词都与第一人称复数的“我们”联用,表明这是作者和读者日常经验中都很熟悉的例子。与耶稣一样,雅各也知道如何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来生动地说明属灵教训。
②船和舵(4节)
或者用船为例。尽管它们如此巨大,又被大风驱使,它们却被非常小的舵操纵,随着掌舵的意思而行。或者用船为例(idou kai,字面意思为“另外,看哪!”),直接转到了另一个例子。感叹性小品词“看哪!”(idou)在这封信中出现过6次(3:4、5;5:4、7、9、11),利用生动的写作风格唤起读者对接下来内容的重视。“另外”(kai)一词置于感叹词之后,字面意思是“看哪!另外还有船”,将这个例子与前一个例子相联,进一步证明了小小的东西可能蕴含极大能力的事实。施蒂尔提议说,这是“人利用机械制造术征服无生命的自然,利用其自然元素的例子”。[27]
对于“船”的尺寸和运动,雅各显然很有兴趣。两个描述船只的分词短语暗示,他对当时的海船有所了解。尽管相关代词如此巨大是用来和小小的舵进行对比的,但这个短语暗示,当雅各看到巨大的海船时,心里曾经充满了惊奇。有些古代的船只十分庞大。保罗前往罗马途中遇难沉没的商船,载有276名乘客,还有大量的小麦(徒27:37-38)。布莱洛克(Blaiklock)说,有人曾提及一艘古代的商船“载着足可以让整个阿提卡人(Attica)食用一年的食物”。[28]
雅各进一步刻画说,这些船只又被大风驱使。尽管这些巨大的船只不像马匹那样有自己的意志,但它们受到外部暴烈的自然力的击打。雅各将这些风刻画为大风(sklērōn)或者“强硬的”风,暗示这些大风绝不会自行改变方向。当大风驱使着船的时候,若缺少有效的控制手段,它们也可能会让船沉毁。
这里让雅各感兴趣的是,这些船尽管体积庞大,又遭遇大风,却可以被非常小的舵操纵。古代船上的舵是一个突出的桨状物,紧紧地系于船尾。使徒行传27:40是新约中唯一另外用到这个词的地方;这里的复数表明这艘船有两个舵,分置于船尾两边。和船的规模相比,这舵的确非常小(elachistou)——最高级的形容词突出了这种比对。[29]通过小小的舵来控制船,是多么的重要呀!当生活中的风暴袭来时,求神将他的手放在舵上掌控,又是多么重要呀!不管航道是多么的狭小,神最清楚如何操纵我们生命的航船,直达目标。
这个小小的舵让大船随着掌舵的意思而行。航船的方向不是由大风所决定,而是“被舵手的意思驱动”(美国标准译本〕)。翻译为意思(hormē)的名词,可能指舵手施加在舵上的物理压力,也可能指他心里的想法或意愿。使徒行传14:5是新约中唯一另外用到这个词的地方,在那里它指的是宣教士的敌人们想要用暴力打死保罗和巴拿巴的内心冲动。但是船按照舵手的意愿而行,这一事实暗示他主动地在舵上施加了压力,使得自己的目的可以达成。他内心的意愿必须通过主动采取行动表达出来,这样才能完成必须的控制。翻译为掌舵的(tou euthunontos)之名词化分词,意思是“引导直线前进的人”。其现在时态指出了行为的特征,表示控制船舵的人决定了整个船的航向。
这两个例子清楚地说明,我们需要控制生命中的关键之处。但是,有些学者还想进一步找出这两个示例的寓意。赖克提出,第一个例子刻画了“一个常常讲道的教会领袖”,因此控制着“所有的信徒”;而对于第二个例子,他认为“船代表教会,舵实际上与舌头相似,所以与教会中宣讲神的信息有关”。[30]约翰斯通认为:马代表人性中“邪恶乖僻的自然之力”,必须加以节制;而船代表“诱惑的力量,是世界和世上掌权者的邪恶影响力”。[31]但是我们必须同意普卢默(plummer)的说法:“这样的象征性解释是人自己读进经文里的,并不是从经文中得到的。”[32]
(2)应用于说大话的舌头(5节上)
同样,舌头是身体上的一个小器官,但它却说大话。同样(houtōs)的意思是“所以,按照同样的方式”,表明这是一个对比。马的嘴和身体相比是一个小小的器官,船的舵和整艘船相比也很微小;但是尽管微小,它们却控制了整体。同样,小小的舌头对整个生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佐德易阿特斯评论说:“舌头的存在和动作都不是独立的。它的行动可以让身体的每个部分受益或遭害。舌头不能逃避其责任,也无法推脱自己造成的影响。”[33]
舌头作为说话的器官,在这里仿佛有着自己的人格和行动的大能。它可以说大话(megala auchei,“大事它夸口”)。“大事”一词被放在动词前面,强调了小小的舌头与所夸耀之大事之间的对比。这不是空空地夸口,因为“整个论证现在转向了舌头所具有的实际能量”。[34]意识到自己具有巨大的能力,舌头傲慢地宣扬自己的丰功伟绩。其结果远远超出了夸口的器官本身的尺寸。这个说法在新约中仅见于此。公认经文将这个短语视为一个单词(megalauchei),意为“骄傲,说大话”。于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舌头暴露出自己傲慢的本性。但是,按照文本证据我们更有理由将其分开为两个词;这样的处理也更切合上下文。这个短语标志着作者要从讨论不受控制的舌头转换到由此带来的悲惨结果。
2.失控的舌头所造成的损害(5节下-6节)
大小的对比还在继续,但是现在雅各所强调的是舌头经常带来的灾难性后果。雅各简单地描述了这些后果(5节下),接着详细讨论了不节制的舌头之性质和行为(6节)。
(1)举例说明巨大的损害(5节下)
想想看,一簇小小的火焰可以点燃一片巨大的森林。想想看(idou,“看哪!”),再次唤起读者对这个例子的重视。若把这一句视为新的一节经文,可能会更好一点。
舌头就像火一样,在受控的状态下是一个极为有用的工具,但是若失去控制,将引起多大的混乱呀!“一簇小小的火焰可以点燃一片巨大的森林”,涉及一个英语很难翻译的双关语。希腊文的形容词hēlikos让人注意某个事物的尺寸,或者表示“非常大”,或者表示“非常小”——“极大或极小”。[35]通过上下文,读者通常可以清楚地知道究竟所指的是大还是小。按照字面意思,这个感叹句应该翻译为:“看哪!什么尺寸的火点燃了什么面积的森林啊!”这一句话借用两样东西在尺寸差异上的常识,给出了非常具有戏剧性的效果。原文中主语“什么尺寸的火”[36]与宾语“什么面积的森林”被故意并列在动词之前。森林(hulēn)一词既可以表示一片树林,也可以表示一堆伐倒的原木。新英文圣经采用了后一种解读:“一个小小的火星,可以点燃多大一堆原木呀!”但是森林或许是更好的意象,因为它“更为生动,也更有画面感”。[37]但是艾略特·宾斯(Elliott-Binns)认为,若认定此信写于巴勒斯坦,那么更精确的画面应当不是高耸的森林,而是荒凉的灌木或者乡间常见的丛林。[38]“若在山坡上有这样一片干燥的灌木,简直就像一个火药桶,一点火星就能引起爆炸。”[39]毕晓普(Bishop)指出,在巴勒斯坦干旱的季节,这样的丛林野火可以飞快地扩散开去。[40]动词点燃不如翻译为“燃尽”,它指的是点起一堆火;但是因为没有加以控制,火势变得十分巨大。不受控制的舌头同样可以带来毁灭性的力量和行动。“在人的本性中,可燃的木材几乎遍地都是,一点火星随时可能引发谎言和犯罪的大火。”[41]
(2)失控的舌头有何性质(6节)
也(kai)这个词将前面的例子与这里所刻画的不受控制的舌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雅各展开了一幅更大的画卷:舌头也是火焰,我们百体之中一个罪恶的世界。它败坏全身,点燃他生命的整个轨迹,并且它自己是被地狱之火点燃的。伦斯基的评论很精彩:“从来没有人这样强调过舌头的功用。”[42]
舌头也是火焰,这是对舌头破坏性的一个巧妙的隐喻(诗57:4,120:3-4;箴16:27,26:18-21)。它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力量;不受控制的舌头因为其本性而具有潜在的危险性。
第6节余下部分的结构和意图,在理解上存在若干困难。接下来的部分有五个主格的短语,但是仅有一个直说式语气的动词,标点符号也比较难断。还有人提出这一节的原文可能有损坏或参杂附注。[43]我们也不能确认“一个罪恶的世界”与别的部分有何联系。有些文本编辑和译者认为它是前一部分的同位语;因此新美国标准圣经在这里放置了一个分号,而新国际译本则使用了句号。但是有些解释者相信,这个短语并不太像“火”的同位语。他们给出的另一个方案是将其和后面的短语连在一起,认为它是后面动词(kathistatai)的叙述主格(predicate nominative)。[44]于是,这里的情况就是叙述主格被强调性地提前,放在主语和动词之前,强调舌头确实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我们也无法确定接下来三个分词短语之间的关系。将各种问题累积在一起,加上本来就存在的语法结构上的困难,表明雅各“在谈到舌头可怕的恶行时,因为愤怒而有点语无伦次”。[45]
新国际译本的翻译我们百体之中一个罪恶的世界,将这个短语视为对舌头本性的进一步描述。这种观点解释了原文中第二个“舌头”(hē glōssa)的用法——因为冗余,新国际译本没有译出。于是,雅各进一步刻画说,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ho kosmos tēs adikias)。两个名词前面的冠词,强调了它们各自的特征。世界这个词的词根本来是“装饰”或者“饰物”之意;在彼得前书3:3里,它被用来指称女人的装饰。人们通常用它来表示世界或宇宙,取其井然有序之意。于是,雅各明确地指出,舌头是一个与“罪恶”有关的庞大系统或组织机构,以不公不义为特征。属格的“罪恶”既可以表示一个“由罪恶构成的”世界(属格做主语),也可以表示一个“以罪恶为特征的”世界(属格表性质)。在这封信里,“世界”一词几乎总是带着负面意味;雅各在这里将它与“罪恶”、“不义”相连,就是为人熟知的、不断与基督徒对抗的不公义和邪恶。迪贝利乌斯认为,这个生动的属格短语,源自希伯来语的形容词短语“那罪恶的世界”。[46]按照这样的看法,雅各在这里描述了舌头黑暗的本性。
其他人则认为,雅各想用“一个罪恶的世界”来表达完全不同的意思。鉴于“粉饰世界”之意,他们提出,雅各想要表示的是舌头将罪恶掩饰起来,打扮成吸引人的样子。因此利利的翻译是,“它(舌头)让罪恶充满吸引力”。[47]佐德易阿特斯根据这个词“装饰、装扮”的意思加以注释说:“良善而净化的舌头将会谴责不公义,然而罪恶的舌头却会称赞它、奉承它,将它打扮成公义的样子。”[48]但是很少有人真正接受这样的观点,比如布莱克曼就直截了当地说这是“脱离上下文的异想天开”。[49]
从上下文来看,我们最好认为雅各想要指出,舌头是一个巨大的罪恶系统。在两个名词前面使用的定冠词,表示这是一个具体的说明;舌头的确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因为它包含所有罪恶的特征。舌头可以参与到世上一切的罪中,因此它与这个世界的罪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尽管新国际译本没有翻译,但在第二个子句中重复出现的“舌头”对此加以强调,因为舌头在“百体之中”占有独特的地位。我们身体上再没有任何器官在行恶的能力和影响范围上可以与舌头一较高下。它可以说出各种恶毒的想法与动机,并将各种恶性付诸语言。它是我们百体之恶的一个微观世界。在第一句话中,新国际译本补充了原文中没有的动词,将其译为“舌头是火焰”;但在第二句话中,译者默认使用同一个动词,因此没有译出原文中明确给出的动词(kathistatai)。对于这个动词来说,“是”是一种相对较弱的译法,因为它本来的含义是“放置、指定、造成、构成”。梅厄提出,这个动词“暗示舌头的本性或原始状态并非如此,而是有着某种程度的适应或发展所造成的”。[50]这个动词常常带有被动语态的味道,表示“被设定为”或者“被构成”。但是我们似乎最好将这个词视为关身语态,即“让自己成为……”,暗示“这不是神本来所‘造’的”。[51]4:4也用了这个词相同的形态,而且可以贴切地翻译为“让自己成为……”(美国标准译本)。舌头作为神赋予人自我表达的工具,本是一件奇妙的恩赐,“但是因为它自己缺少约束、无法无天,于是使自己变成‘罪恶的世界’”。[52]
这一节余下的部分没有限定动词,在语法结构上构成‘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的同位语。这一部分由三个分词构成,只有第一个分词短语有定冠词。从语法上看,可能有两种构造。我们可以将所有三个分词短语都归在同一个定冠词下,于是构成一个符合形式的同位语。或者将带有定冠词的第一个分词短语单独拿出来,将其视为同位语,而把另外两个分词短语当作对第一个分词短语的扩展解释。我们认为后一种构造更有可能成立。新国际译本将这一部分处理为一个新的句子,把分词翻译为限定动词。
它败坏全身宣布了不受控制的舌头所带来的恶劣影响。它不仅自己在道德上有罪,而且具有败坏和玷污全身的影响力。带有冠词的主动语态现在分词“败坏全身之物”[53],刻画了舌头逐渐造成道德影响的过程。动词败坏(spiloō)仅在这里和犹大书第23节中出现过,是一个描写道德影响的动词。这个动词的原意是“污秽、玷污”,而在这里带有象征意义,表示因为舌头的影响而造成的道德败坏。在1:27里,雅各使用了同源的形容词之否定形式,来说明真正有信仰的人会保守自己不“被世界玷污”。但是,不受控制的舌头所发出的不洁净的、恶毒的话语“会感染说话人的血液——一种道德上的大麻风病,影响到所有器官并败坏一切的行为”。[54]它传染道德的污秽,并败坏全身(holon ton soma)。在第3节里,雅各用了同样的短语来形容马匹,其译文是“整个动物”。在这里,“身体”一词无疑是指整个人格,因为人格驻在身体之中,使用身体作为工具来行动。
我们通常不会认为火是一种败坏,所以有人认为雅各的思路前后不一,因为他现在开始说舌头“败坏”了整个身体。但是这一节余下的部分,在继续火焰之意象的同时,说明了这种道德败坏的影响过程。
接下来的两个子句点燃他生命的整个轨迹,并且它自己是被地狱之火点燃的,由两个分词短语构成。这两个分词彼此关联:它们都来自同一个动词“点燃”,其时态也完全相同;第一个分词的主动语态与第二个分词的被动语态构成某种平衡;两个子句都用了kai,暗示可以翻译为“二者……都”。我们认为,这两个分词都是在修辞前一个带有定冠词的分词短语——“玷污全身的”(美国标准译本)。它们解释了不受控制的舌头所具有的恶毒、败坏之功能。
短语点燃他生命的整个轨迹,其含义不明。人们就此提出了各种翻译方法:“点燃自然的循环”(setting on fire the cycle of nature,修订标准译本);“点燃实存的圆圈”(setting fire to the round circle of existence,莫法特译本);“它让我们实存之轮灼热燃烧”(it keeps the wheel of our existence red-hot,新英文圣经);“点燃我们生命的整个轨迹”(sets the whole course of our lives on fire,韦茅斯译本);“是起源进程的燃烧器”(is the inflamer of the process of generation,斯科菲尔德译本)。
短语他生命的整个轨迹(ton trochon tēs geneseōs)中的两个名词,都可以有不同的含义。在希腊文里,第二个名词就是英语的genesis,表示“诞生”(例如美国标准译本的页边注)或者“起源”(太1:18;“起源”的历史),或者可以表示“存在”,就像雅各书1:23的用法(“他天生的面容”,美国标准译本),也就是他实际存在的面貌。前一个名词,根据希腊文中重音位置的不同,可以表示“轮子”或“轨迹”,或者围着圆圈“跑步”的意思。蒲草纸抄本的用法似乎更偏向于“轮子”的译法。在这里,它似乎暗示某种循环的动作或存在。
有人提出,雅各可能是从教导灵魂不断轮回、生命是一种无聊轮回过程的俄尔普斯神话(Orphic Mysteries)中借来了这个短语[55],但这种看法不太可能。不管这个短语来自何处,雅各都不太可能是要表达轮回的概念。他也不会希望读者从这句话中得出这种概念来。作为一个注重实际的人,雅各期望读者按照生活常识来理解这句话。
有人提出,雅各想象生命是一个轮子,从出生一直滚向死亡的终点。或者他想象日常生活像一个轮子,每日重复着同样的事务。有人甚至详尽地描述说,舌头就是轮轴,若被火点燃,整个轮子就都陷入了熊熊烈焰之中(参见上面给出的新英文圣经)。
根据上下文,似乎雅各所谓“他生命的整个轨迹”并不仅限于一个人的一生。新国际译本中的代词“他”并不见于希腊文原文,我们似乎也以删除它为好。鉴于前一个短语提到舌头对一个人“全身”的影响,这一个短语似乎意在说明不受控制的舌头所具有的广泛社会影响力。雅各似乎心里想着人类存在的整个转轮,而个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这个短语表达了人生中各种关系都会因不受控制的舌头而变得紧张的意思。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不加考虑的、恶意中伤的说法会让整个共同体陷入混乱;某些恶毒的宣传可以让整个民族陷入狂热,让不同的阶级陷入彼此毁灭的冲突中;粗野的、充满激情的民族仇恨,可以引发国际冲突,直到血流成河方才止息。同样,“恶意的道德教训、流行的宗教以及教义上的错误,可能像巨大的火山爆发一样,埋葬数不清的受害者”。[56]不受控制的舌头的确能在人群中产生同样的毁灭效果,就像一点不受控制的火星点燃整个森林一样。
并且它自己是被地狱之火点燃的,揭露了舌头所蕴含的毁灭性火焰的来历,为整个画面补充了深刻的属灵含义。正如布卢所说:“舌头只是导火线,死亡之火的源头来自地狱本身。”[57]不受控制的舌头之恶,与不可见的灵界之恶有关。“唯有(启示录所描述的)第二次死亡的火湖,才有可能点燃舌头所散布的毁灭性大火。”[58]这个现在时态的被动分词暗示,不受控制的舌头一向是被地狱之火点燃的。它放纵自己,允许自己被撒但之恶所利用。
地狱(geennēs)这个词除了出现在同观福音书(译注:参太5:22),便仅见于此。它是希伯来文ge-henom(“欣嫩谷”,或者全称“欣嫩之子的山谷”)的希腊文写法;这个山谷位于耶路撒冷城墙西南方向偏南。在亚哈斯和玛拿西做王的时代,人们在谷中将自己的孩子献祭给异教的神摩洛(代下28:3,33:6)。但约西亚登上王座之后,他“污秽”了这地(王下23:10),不允许人再在那里用儿童来献祭。后来,那个地方变成耶路撒冷城的垃圾场,终日有火在其中焚烧,销毁垃圾和污物。这是一个被污秽、火焰不断燃烧的地方。这个场面被认为与罪人将要受到最终审判的场景非常相似。[59]耶稣使用gehenna[60]一词,宣布罪人要在地狱受惩罚,“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可9:48)。人们认为,Gehenna就是“火湖”(启19:20,20:10、14、15)。
但是雅各把舌头和地狱关联在一起,并不是要说地狱是舌头犯罪应受惩罚的地方。他心里所想的是,舌头唤醒了本已打入地狱的魔鬼,任其不断地激发人类的恶行(参3:15)。不受控制的舌头太容易成为撒但及其差役的工具,用来散布地狱的火焰。这句话并没有阻碍雅各的目标,即阐发与之相反的真理——有节制的舌头同样可以被神的圣坛之火点燃,用于服侍神的目的(赛6:6-9)。
(三)舌头具有无法制服的性质(7-8节)
第7节开头的“因为”(gar,新国际译本未译出)证实了舌头的可怕之处,甚至连人类也无法制伏它。兰格(Lange)认为,这句话和前一句话的关联之处在于舌头是被地狱之火点燃的。[61]但是,若我们将其看作对第5-6节整个可怕场面的证明,可能会更为妥当一些。雅各的证明以对比的形式给出。人类在制伏动物上显露出惊人的能力(7节),然而却无法制伏恶毒的舌头(8节)。
1.动物可以被制伏(7节)
各类的走兽、飞禽、爬行类,以及水族,本来都可以制伏,也已经被人制伏了。古代世界对于人类可以制伏、驯化和控制动物王国颇感骄傲。诗篇8:6-8称赞了神赐给人管理神所造一切动物的能力。在这里,雅各并不是说所有被造物都已经被人的技艺和才能驯服;他也不是在坚持说每种动物都已经被人驯服。名词类(Phusis)的意思是“天性”,指的是将整个动物界分为不同种群的天生特征。通过在这一节里2次使用这个词,雅各清楚地对比了动物的天性和人类的天性,说明后者支配着前者。各类的(pasa phusis)受造物组成了动物界,而“人类”(tē phusei tē anthrōpinē,“人的天性”)已经控制了它们。
雅各对动物界的分类可以在创世记9:2和列王记上4:33中找到相关经文(参创1:26)。它们被分为两组:行走的和飞行的动物,似乎是更为高贵的品种;以及爬行的和在水里游泳的动物。这不是什么科学的分类,但是对于雅各所要讨论的问题而言,已经足够了。走兽表示四足的动物,但是这里似乎指的是“野兽”,因为作者没有必要强调人类可以驯服家畜。爬行类本来常用作指蛇,但这里所指的范围要更广泛一点。水族(enalion)一词在新约中仅见于此,但是在世俗的希腊文中十分常见,指的是生活在海里的鱼和其他各样生物。
制伏并不表示已经驯养或者驯化。原文所用的动词比“驯养”要强烈,意思是“征服、控制、使某物服从”在人类的目的之下。除了这里,新约只有马可福音5:4还用到这个词,用来形容格拉森被鬼附之人无法被人控制。许多野生动物都已经被人征服,但并不能加以驯化到这样的程度,可以安全地取掉约束它们的锁链。
雅各在这里2次使用了“制伏”一词,一次是现在时态,而另一次是完成时态,是要提醒读者注意从日常观察和历史中得出的证据。现在时态的动词描绘了读者可以反复观察到的人类制伏动物的事实。正如基斯特梅克所说:“我们在马戏表演中可以看到野兽顺服自己的驯兽师,只要甩一下鞭子、打一下响指、拍一下手,它们就听命而行了。”[62]完成时态的已经被人制伏了进一步指出,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例子。人类这种奇妙的能力并不新鲜;它是神创造人类的本来目的之一(创1:26,9:2;诗8:6-8)。这是人类在本性上高于动物的明证。
2.舌头无法制伏(8节)
但是一词引出了下面令人伤感的对比:但是没有人可以制伏舌头。现在时态的可以(dunatai)或者“能够”,宣布说人类一直不能有效地“制伏”(不定过去式)舌头。“因为堕落的缘故,”塔斯克说,“人类失去了把握自我的能力。”[63]舌头一词被强调性地提前,表示人类的舌头是“独一无二的被造物;也就是说,是无法制伏的!”。[64]由属格名词人(anthrōpōn)所限定的没有(oudeis),被强调性地放在句尾,排除了任何例外情况。“这种无能为力纯粹是道德意义上的,其原因是意志的缺乏。”[65]但是,堕落人类的绝望处境,可以显明神的恩典和大能。
有些解经家认为,雅各的意思是,尽管人可以控制动物,但他无法控制其他人的舌头。然而这里整个讨论的要点,是人不能控制自己的舌头。
雅各进一步描绘了人所不能控制的舌头的两个特性:它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致死的毒。这两个短语中没有限定动词,因此可以视为“舌头”(tēn glōssan)的同位语,但是这样一来,就要求打破语法规则,将主格的mestē(满了)充作直接受格名词的同位语。一般而论,这两个短语都可视为叙述主格,而按照新国际译本的做法,补充缺省的系动词是。但是,更有力的解释似乎是将它们都视为道德上发怒的感叹,因此不需要任何系动词:“不止息的恶物!满了致死的毒!”[66]
形容词不止息的(akatastaton),在1:8里被译为“没有定见”。它将舌头刻画为反复无常而且善于变化的东西;人们不能信赖它可以顺从地待在自己应该待着的地方。舌头出了名的不可靠,不断喷发出恶毒的言辞。这里的形容词暗示“某些关在笼子里但尚未制伏的野兽,不停地在其中来回地巡走踱步”。[67]这不止息的舌头之本质是恶(kakos),下流、堕落、常常出口伤人。
英王钦定本根据所用的异文(akatascheton,“不受控制、无法约束”),将这句话翻译为“难以管束的恶”(an unruly evil)。但是这种异文并没有很好的证据支持,对整个画面也没有什么补益。
舌头的影响是致命的:满了致死的毒。致死的之字面意思为“孕育死亡的”,可能是暗指毒蛇的舌头(诗58:4,140:3)。这个形容词在新约中仅见于此。而用毒这个词来形容恶毒的舌头致死的作为,实在是一个巧妙的用法。
“从古蛇口中吐出的恶毒言语让人类陷入死亡,而撒但之子的舌头,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撒但的舌头一样恶毒。”[68]
(四)舌头具有前后不一致的性质(9-12节)
雅各承认,舌头可以从事赞美神的高贵工作,也可以用来咒诅人。这种双重功能深刻地显明了它在道德上的邪恶,让它应受加倍的责备。雅各说明了这种极大的不一致性(9-10节上),对此加以谴责(10节下),并用自然界的例子说明这种扭曲(11-12节)。
1.说明这种不一致性(9-10节上)
这一节没有任何连接性小品词,因此标志讨论进入新的段落。我们用舌头赞美我的主和天父,也用它咒诅人,就是那照神的形象被造的。用舌头(en autē,“用它”)承认了舌头仅仅是说话的人用来自我表达的工具。这个表达在下一句中反复出现,强调了这一事实。尽管雅各以务实的态度拟人化了舌头,但他完全清楚,是背后的人在操控舌头。“我们”这个词指出,滥用舌头是人类的普遍特征,雅各承认基督徒也并不例外。甚至信徒也可能犯下言行不一之罪。“赞美”和“咒诅”都是现在时态,表明舌头可以同时扮演《化身博士》中的好人杰基尔与恶人海德,而且这并非孤例。它被用在“毫不相干的活动上:一方面它非常敬虔,但是另一方面,它在日常生活中有可能极为亵渎”。[69]
我们用舌头赞美我们的主和天父,说明了人类舌头至高的、最为尊贵的用途。赞美(eulogoumen)的意思是“说好话,颂扬”。当神是赞美的对象时,这个词的意思是称颂他的名和作为。我们赞美的对象是我们[70]的主和天父[71]。这是新约中十分独特的短语。这两个称号由共同的定冠词联系在一起,指向神的权柄和权能,同时也指向他的爱和怜悯。圣经同时启示了神在这两个方面的属性。“‘天父’一词,”沃尔夫说,“说明了神与人的相似之处,并且强调他的爱与彼此仇恨的人们相互咒诅形成尖锐的对比。”[72]
犹太人在提及或书写神的名字时,总是会加上“赞美神”这几个词,视其为一种敬虔的做法。无疑,当提到神的名字时,这封书信的读者们也会延续这种做法。每一位基督徒的舌头也应当如此赞美神。
也用它咒诅人,将舌头的恶毒用法与前面高贵的用法排列在了一起。用它,再次说明舌头只是用来表达说话人内心感受的工具。动词咒诅(katarōmetha)的字面意思是“宣告咒诅落在某人头上”。佐德易阿特斯说:“为了宣告诅咒落在某人头上,一个人一定认为自己的地位较高,因此可以将自己贬损的话语倾泻到某人的头上。”[73]奥斯特利指出,这个词表示“人格羞辱,就像在激烈的争吵中暴跳如雷地说话一样”。[74]这里不是指用低俗的语言来亵渎、冒犯他人,而更像是在教会内的纷争中(参4:1-2,11-12)恼怒地争吵和恶语伤人,从而失去了自我控制,引发了恶毒的咒诅。“我们”一词并不暗示雅各自己在这上面犯了罪,而是说甚至包括雅各本人在内的基督徒们,有时也会落入这样的罪恶中。
咒诅人(taus anthrōpous)是针对同为“人类”的别人犯下的一种特别的大恶;这一点由补充的同位语就是那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予以强调。完成时态的被造,表明在创造时赋予我们的神的形象,至今并未完全丧失。这里所指的是人现在的状态。罪在堕落的人身上严重地破坏了神的形象;然而,作为神最高贵的受造物,每个人都依然保持着“不可摧毁的高贵”[75],这宣告他在一切受造物中拥有最高的冠冕——从神而来的形象和尊严。堕落之人实在是“一件丑闻”,但是神指派他代表自己掌管万物(创1:26;诗8:4-8),因此他也是“宇宙的荣耀”(帕斯卡〔Pascal〕)。神的形象,主要表示人是拥有人格、理性和道德之存在。他超越神的所有其他受造物,单独拥有理性、意志和良心,有能力认识和服侍神,可以在道德和属灵上与神相像。因此,咒诅人就是在嘲讽神,因为人的身上带着神的形象。施蒂尔评论说:“因为圣雅各向着弟兄们说话,他并没有明确地提出,这是直接针对神的公开亵渎;但是,他清楚地表明,伤害和羞辱人,与攻击神的形象同罪。”[76]相反,因为人有着与生俱来的尊贵,所以我们应当尊重和善待他们,即使他们有时会给我们造成不快和可能的伤害。
雅各附加的评论从同一个口里出来颂赞和咒诅(10节上),揭露了这种致命的不一致。这里所强调的是从同一个口里。从同一个口里轻易地流出祝福与咒诅,证明其源头在道德上的乖张。马丁说,“从舌头到口(stoma)的切换值得加以注意”,因为它强调了“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太15:11、20)”[77],表明雅各完全赞同耶稣关于话语能污秽人的教训。对神的赞美失去了高贵的品质,因为咒诅之苦毒而变得污秽不堪。当人对带着神形象的其他人心存苦毒仇恨时,他对神的赞美、称颂不可能被悦纳(参约壹4:20);无疑,雅各曾经在法利赛人身上看到过这样的情况——他们夸耀自己是百姓中敬虔的领袖,但是常常咒诅众人(约7:47-49)。雅各也可能从一些人的身上看到这种精神,他们“恶声恶气地瞧不起彼得传福音的对象(徒11:2-3),或者不仅拒绝宽容,还想将未受割礼之人排除在救恩之外(徒15:1)”。[78]
2.谴责这种不一致性(10节下)
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这个责备十分温柔,充满爱心。雅各视为我的弟兄们的人,身上有着这样的不一致,这让雅各倍感忧伤。“当他不再谴责罪的可恶之处,而是对待羞愧的罪人时,道德上的愤怒就止息了。”[79]
动词应当(chrē)在新约中仅见于此;它带有合适、恰当的意思。他们身上有着这现象(tauta,“这些事”),即赞美神却咒诅神的家人,显出了某种被天性和恩典所拒斥的道德异常。雅各还加上了一个新国际译本没有翻译的副词houtōs(“这样,如此一来”),概述了这种不和谐的情况。这样强烈的表达方式,清楚地说明在他们中间不应当容忍这样明显的恶行。在弟兄们中间,这种行为完全不恰当、不合时宜。
3.用自然的一致性来定罪(11-12节)
雅各再次从自然界举例,证明了如此说话是不一致的。甜水和咸水可以从同一个泉源中流出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或者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11-12节上)?这些问题强烈地要求读者给予否定的回答。新国际译本没有翻译的疑问助词mēti,带有“他们肯定不能这样做,是吧?”的意思,暗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让答案呼之欲出,毫无疑义。同一个泉源表明了物质界的一致性,谴责了人类刺目的不一致。罗瑟拉姆译本更为字面的翻译“从同一个开口出来的泉水,可以同时是甜水和苦水吗?”,表明代表其所属类型的“那泉水”(hē pēgē),没有像人的口同时说出祝福与咒诅的话那样显露出不一致。
在干旱的巴勒斯坦地区,所有的读者都应当明白泉水的重要性。许多村庄的存在,有赖于周围有这样的水源。从泉眼出来的水长期保持清洁可用,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动词流出(bruei)在新约中仅见于此,表示某物充满而溢出;它表示泉水自己溢出泉眼。但是依靠这泉水的旅人或者村里的居民,不希望悬崖上开口的泉眼有时流出清洁的、可以饮用的甜水(to gluku),有时却流出又咸又苦、无法饮用的咸水(to pikron)。尽管有着清楚的暗示,但原文没有使用“水”这个词,而是让“甜”和“咸”这两个形容词构成更加尖锐的对比。世上没有任何泉水会如此又甜又咸。
果园和葡萄园也不能如此变化多端(12节)。能(mē dunatai)这个词要求读者坚定地回答“不”;无花果树绝不能生橄榄,葡萄树也绝不能结无花果。它们必须按照自己的种类结果子。雅各让人回想起耶稣的教训(太7:16-20)。插入的直接呼语我的弟兄们,表明雅各感情充沛地想要引导其他信徒明白他的要点。
无花果、橄榄和葡萄是巴勒斯坦的三种主要出产物。雅各诉诸这一类熟悉的对象,再次表明他能够通过身边的物质世界来表达必要的属灵教训。“正如无花果树不能结橄榄,或者葡萄树不能结无花果,清洁的心也不能产生虚假的、苦毒的、有害的言语。”[80]
雅各用一个肯定的断言结束了这一教训: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81]这是取自巴勒斯坦自然环境的另一个例子。凡是看到过死海附近众多盐泉的人,都不能想象会发生这样不一致的事情。咸水(halukon)只是一个简单的形容词“咸”;这个形容词在新约中仅见于此。在这一节里,人们普遍将其理解为“咸泉”。在七十士译本里,这个形容词被用来指称“盐海”(民34:3、12;申3:17;书15:2、5)。但不管是盐泉还是盐海,都不能流出甜水来。大自然自有其运行之道。“自然界的每件事物都按照神的命令运行至今,万事万物都服侍他;只有人类歪曲了世界本来的秩序,竭力阻止神与疏离的大自然重新联合在一起。”[82]雅各坚持认为:“从基督徒心里流出的话语,必须与其对待神和神的创造物之行为一致。”[83]
雅各没有从所举的例子中得出任何结论。但是这些例子对人类的不一致之谴责是如此明显,因此没有必要再给出进一步的应用了。
(五)控制舌头的智慧(13-18节)
雅各没有使用连接性小品词,将这一段与前面所说的紧密地联系起来。有些学者,例如迪贝利乌斯,断言事实上这两段“在思路上并无联系”。[84]但是人们一般认为,它们之间至少存在“松散的联系”。普遍的看法是,这一段“直接恢复了本章开始处第1-2节上的警告”。[85]于是,这几个经节可以认为是直接针对教会里做教师的人说的。尽管这一段特别针对基督徒中做教师的人,但我们完全同意米顿的看法:“这一段里没有任何教训不能同时应用在教师之外的基督徒身上。”[86]把这一讨论两种智慧的段落,视为从整体上扩展了对舌头功能的讨论,似乎是一种更好的看法。这些经节进一步讨论了第9节所给出的基本真理——舌头是揭露人内心状态的工具。舌头的使用揭露了控制一个人的灵性状态是怎样的,可以看出一个人有没有从上头而来的智慧流出。这些重要的经文,让雅各书不负新约里的“智慧书”的美名。
在第13节里,雅各挑战读者通过良好的生活显出他真有智慧。这一考验可以揭露两种不同的智慧:雅各首先刻画了被假智慧控制的证据(14-16节),接着给出了真智慧掌管人生的证据(17-18节)。
1.有智慧的人应当如何显示智慧(13节)
雅各首先用一个探索性问题来提出他的挑战: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这种带着个人关怀的提问方式,直接诉诸每一个读者的良心。他的提问并不暗示说无人有智慧,而是挑战那些匆忙断定自己有智慧的人,让他们仔细地进行自我检查。
这种修辞问句的手法,是希腊哲辩形式的特征。但是这并不暗示雅各试着采用希腊作者的手法,因为这种众所周知的文学手法并不是他们所独有的。耶稣(例如,太11:16;可4:21、30)和旧约作者(诗15:1;箴6:27-28,8:1;赛50:1;弥4:9)也经常使用这种手法。作为一个老练的演说家,雅各熟知这种方法的价值。布莱克曼说,这种特征“也是我们作者的特点,而且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这种风格就代表了他本人’”。[87]雅各也可能把他的挑战写成了一个条件语句,但这样一来就会减弱挑战的力度。
“智慧”和“见识”这两个形容词连用,在新约中仅见于此。它们曾经用在申命记1:13(七十士译本)里,用来描述以色列各个支派中士师所需的品质;但是在申命记4:6和何西阿书14:9中,它们被用在一起,形容神的所有百姓所需要的品质。显然,雅各期待读者中做教师的人要特别注重这样的品质,但它们应当是一切真信徒的标志。它们的连用,强调了神所要求的关键道德品质。
在犹太人的用法中,智慧(sophos)表示一个人拥有道德洞见和技巧,可以帮助他在实践中做出正确决定——这是一种从认识神而来的智慧(参1:5以下注释)。见识(epistēmōn)这个词在新约中仅见于此,被用来形容一个知识丰富的专家,可以在实践中充分应用自己的知识。这两个词是同义词,我们无法确定它们之间细微的差别。也许第一个词表示道德品质,而第二个词表示智识品质。作者在这里希望读者不仅具备学术知识,也应在实践中体现出道德和属灵的洞见。
雅各期待人自己意识到自己的状态,还是希望别的人看出他的状态来?似乎他想表达的是前一层意思,因为他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愿他通过他良好的生活,通过来自于智慧的谦卑行为显明出来。雅各要求智慧与信心一样(2:14-26),可以通过行为证明出来。不定过去式的祈使语气动词愿他……显明出来(deixatō),要求人有效地证明这一点。他所需要的证明不是可以在辩论中机智地得胜,而是通过他良好的生活来证明。通过(ek)一词更好的翻译是“从中而出”,指的是得出证明的总体源头。(请比较2:18完全一样的平行经文:“通过我的行为。”)因此,他的证明必须出自他良好的生活。名词生活(anastrophēs),表示“行事为人的生活”[88],或者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小事。[89]他的社交行为应当被众人视为良好的(kalōs),即“高贵的、优美的、有吸引力的”。他可爱的日常行为,应当显明他有着所需的实践智慧与见识,可以处理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问题。“真智慧的标志不是一个人有着正统的教义(正确的讲道),而是他有着正统的实践(正确的生活)。”[90]
他吸引人的一生,必须“通过来自于智慧的谦卑行为显明出来”。作为智慧的试纸,一个人的行为必须通过他的信心才能达成,它提供了神改变生命的大能在他里面动工的外部证据。
他的行为必须是来自于智慧的谦卑行为。这句话强调谦卑(prautēti)的态度,但更常见的翻译是“温柔”或“温顺”。这种“温柔”是真智慧的特征,与狂傲的自以为是正好相反(参1:21下)。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态度,让他与人交往时生出温柔和善;它不是一种弱点(太11:29),而是一种把控权势、不至张狂的能力。温柔的人不需要为了让别人承认他的权利而斗争,也不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个人观点。谦逊、不爱出风头,是他生活的特征。“基督徒的温柔,”莫说,“包括我们健康地认识到自己在神前面的不配,以及在对待他人时有相应的谦卑和抑制骄傲。”[91]可以理解的是,这种温柔的态度并不被非基督徒的世界所称赞和欣赏。
2.假智慧控制我们的证据(14-16节)
开头的但是(de)一词,指出若他们中间缺少“来自于智慧的谦卑行为”时,必然会发生的事情。雅各没有精确地指出,与这种智慧所生出的温柔相对的到底是什么;相反,他继续刻画了当我们被两种不同的智慧控制时,各自可能出现的后果。如果他们被“苦毒的嫉妒和自私的野心”控制(14节),就是拥有假智慧的明证(15节),因为随之而来的恶毒纷争,将会证实这种状态(16节)。
(1)假智慧的暴露(14节)
但是,如果你们心里怀着苦毒的嫉妒和自私的野心,就不可为它自夸,或者否认真理。条件语句“如果你们心里怀着……”,略微软化了这幅悲惨的画面,但也暗示了这种状况的现实存在。[92]怀着(echete,“有”或者“持有”)似乎暗示情势不仅已经爆发出来,而且每个人还暗暗怀着这样的心思。[93]
苦毒的嫉妒,是他们的态度中两种恶劣因素之首,同时也被强调性地放在动词的前面。名词嫉妒(zēlon)的希腊文形式,就是我们英文单词zealous(“热心”)的来源。这是一个中性名词,既可以作褒义(约2:17;林后7:7,11:2),也可以像新约中占据主流的用法一样用作贬义。这里,雅各通过形容词苦毒的(pikron),强调了其贬义。第11节用了这个形容词的字面含义“咸的”或苦的水;但这里的用法是修辞性质,表示苦毒、严厉的态度。当用作贬义时,这个名词表示“妒忌“或“嫉妒”。现代各种译本有的将其译为“苦毒的嫉妒”[94]或“苦毒的妒忌”(新国际译本、拉蒂译本、韦茅斯译本),有的译为“苦毒的争竞”(达秘译本)或“苦毒的狂热”(杨译本)。鉴于这里所指的似乎是一种被宗教驱动的情绪,“苦毒的狂热”或“严酷的狂热”似乎是最佳翻译。宗教狂热或向神和真理“大发热心”,是一种受到称赞的态度,但是人的罪性可能阴险地利用它,用来苦毒地反对那些用与我们不同的方式表达他们对神和真理之信仰的人。如果这里所讨论的仅限于基督徒中作教师的人,那么就是指宗教领袖们为了赢得更多追随者,彼此嫉妒竞争。但是在他们的追随者身上,同样可以轻易地发现这样的态度。
这种对宗教狂热的暗示,同样体现在他们态度的第二种恶劣因素中:他们怀着自私的野心(eritheian)。这里的名词前面没有附加形容词,这个词的精确含义也属未知,但是其邪恶之处是显然的。在新约之前,我们只见过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使用过这个词,指“采用不公平的手段自私地竞争官职”。[95]目前,大多数人认为这个词不是来自eris(“争斗”),而是来自erithos(“雇佣的仆人,为了工资而干活的人”),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20和加拉太书5:20里所列的恶行中同时包括这两个词。这个词的基本含义似乎是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好处,采用不道德的方式竭力推销自己的计划。因此,它带有分门结党、派系斗争的意思。在新约用到这个词的所有地方(罗2:8;林后12:20;加5:20;腓1:17;雅3:14、16),它似乎都是这种含义。[96]因此,它表示人愿意“用不道德的、引起分裂的方式”来推动自己的观点或促进自己的利益。[97]这是一种伤害基督徒团契关系的可悲情绪。
通过补充你们心里几个词,雅各提醒读者,问题不是出在外部,而是存在于他们的内心。这个短语可以同时用于这句话的两个名词上。不管是“苦毒的嫉妒”还是“自私的野心”,都是他们内心强烈的行事动机。内在的邪恶冲动,而非圣灵,才是他们行恶的真正源头。雅各从神的立场刻画了他们的行为。在希伯来人的思维中,心是道德行为之源头(箴4:23)。雅各提醒读者,“如果‘从心里发出各种恶事’,那么再大声地虚伪宣告自己有‘智慧’也没有用处”(参太15:19-20)。[98]
雅各在谴责他们内心邪恶的态度时,向读者提出了两个要求:不可为它自夸,或者否认真理。他只用了一个否定词(mē),但无疑同时管辖这两个动词;否定词加上现在时态祈使语气动词,要求他们停止这些暴露内心态度的行为。
复合动词自夸(katakauchasthe)的意思是“夸口,得意”,带有自以为比人优越而志得意满、幸灾乐祸的意思。因此,它表示在与对手争论的时候,“因为自己一党所获得的微不足道的优势而恶意地夸胜”。[99]这是他们苦毒的狂热和结党纷争的想法自然结出的果子。在2:13里,雅各用这个动词来形容将来审判之时怜悯向严厉的审判夸胜;在这里它描绘的是在日常交往中有人狂傲地向别人夸胜。希腊文原文中没有的它这个词,于是既可以指他们自以为比人多掌握了真理,也可以指他们自以为拥有的“智慧”。布尔特曼(Bultmann)指出,这个复合动词在圣经和基督教文献以外只出现过一次。[100]似乎是基督教使这种邪恶受到公开的良心谴责。
雅各进一步要求他们不要否认真理(kai pseudesthe kata tēs alētheias,字面意思为“不要说谎对抗真理”)。对于这里的“真理”,人们有着不同的理解。它也许指具体案例中的事实,就像马可福音5:13所陈述的一样;佐德易阿特斯认为,“它的意思就是正直、诚实、忠诚,与谎言相对”[101],或者指的是福音的真理(1:18,5:19)。最后一种理解在这里似乎比较恰当,因为它全面地暴露了他们罪过的严重性。他们的态度和行为抵挡福音的“真理”,而作为基督徒他们却号称接受真理、传播真理。
短语“抵挡真理”既可以配合前面两个动词,也可以单独用在后一个动词上。迪贝利乌斯接受前一种观点,但是指出“这种用法有点失之冗余”,因为雅各只是简单地表示,“不要夸口和说谎抵挡真理”。[102]但是其他人,比如梅厄[103],更倾向于认为“抵挡真理”单独用在第二个动词上。这样的理解更为有力,而且避免了重复的表达。于是,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动词视为表现原因与结果:“不要夸口,以至于说谎抵挡真理”(新美国标准圣经)。[104]戴维斯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这句话的含义都很清楚:那些一心结党纷争、充满苦毒狂热之人,至少应当诚实地面对自己,停止声称自己得了神上从天赐下的智慧之启示。”[105]
(2)假智慧的特征(15节)
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不属灵的,属鬼魔的。这样的“智慧”(hautē hē sophia),总结了第14节所描述的景象。缺少温柔,产生嫉妒、自私的野心与苦毒的冲突之智慧,也许可以称之为“智慧”,但是绝不可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全备的赏赐”之一。如果雅各知道如何使用引号这种当代文学工具,他无疑会在这个词上添加引号,就像新国际译本所译的那样。
从消极的观点看,实际上他们所声称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不具备从天而来的智慧之特征。它们算不得真正的智慧。
从积极的观点看,“这样的‘智慧’”是属地的,不属灵的,属鬼魔的。这三个形容词“层层累进地表达了与神疏远的意思”,构成了批判的顶点。[106]每个词的重要性都由它们各自的反义词凸显出来。
属地的(epigeios)一词,说明它“被地拘束”(新英文圣经),标明它与“从上头来的”(希腊文)智慧构成尖锐的对比。“表面上看,”戴维斯说,“说某物属地并不是一件坏事,但如果有人声称它是从神而来的,那就坏了(林前15:40)。”[107]因为,“属地”的东西来自于没有重生的人性,受到脆弱而有限的生命限制,与地上混乱的状态有关。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里,保罗责备好争辩的哥林多人,他清楚地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智慧:“世上的智慧”(1:20,2:5-6)与“神的智慧”(1:24,2:7)。
形容词不属灵的(psuchikē),来自于名词“灵魂”(Psuchē),意思是“与属灵的生命有关”。圣经用这个形容词来表示“自然世界的生命及其所有的一切,与超自然的世界相对”。[108]这个词并不表示肉体所有的私欲,而是指人的本质中与神隔绝的那一部分,与神所赐予的生命相对——因其缺少神的灵,所以被称为“不属灵的”。按照帖撒罗尼迦前书5:23的三分法,这个形容词描述了人与周围动物界所共有的、非物质存在的部分。它指的是未重生的人性之力量和禀赋,就如人从亚当身上所继承的那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14里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就带有这样的含义:“属血气的(psuchikos)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美国标准译本)。因此,这个词在这里描述了从堕落的人性之精神和情感冲动中发出的智慧,以其败坏的本质、欲望和企图为特征。
属鬼魔的(daimoniōdēs),其字面意思是“鬼魔一样的”,表明这种“智慧”具有魔鬼的特征。这个形容词在新约中仅见于此,它引申自常见的名词daimonion(“鬼魔或邪灵”),指的是带有邪灵的特征或者从邪灵而出的东西。这个词并不与魔鬼的位格有关;圣经从来不把撒但称为鬼魔(demon),他所统领的众多臣属也从来没被叫做魔鬼(devils)[109]。只有一个魔鬼,就是撒但;但是有数量庞大的鬼魔推进撒但的工作。雅各所指的,是那些不洁净的邪灵——他经常看见被它们附体的可怜受害者(参2:19)。在提摩太前书4:1里,假教义被认为是受到鬼魔的影响。在这种以嫉妒、狡猾的结党纷争和自高自大的吹嘘为特征的“智慧”背后,雅各发现有鬼魔在工作,想要败坏基督身体的和谐与生命。
在基督教会以后的日子里,当教会与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的异端观点斗争时,曾认定这种自称优越的属灵洞见是出自鬼魔。但是我们没有证据认为,雅各所谴责的这群主张“智慧”的人,就是早期诺斯替主义的支持者。迪贝利乌斯在总结他的研究时这样说:“没有理由认为雅各是在讨论诺斯替主义,或者直接针对其观点。”[110]
(3)假智慧的结果(16节)
因为一词,让雅各可以引申出他强烈谴责这种“智慧”的理由。“因为你们在何处有嫉妒和自私的野心,你们就在何处可以找到扰乱和各样的恶行。”因为它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所以这种智慧应当受到谴责。“在何处……就在何处”,说明了这种智慧的外在表现(14节)与其社会后果之间的联系——二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联系。
雅各宣告说,“苦毒的嫉妒”(14节)之必然后果就是带来扰乱(akatastasia),指明了这种“智慧”之混乱效果。在1:8里,雅各用它的形容词形式来描述心怀二意对人所造成的影响,而在3:8里,则用它来描述不受控制的舌头。在这里,这个名词表示“智慧”在教会里公开所造成的混乱、失序和混沌不清的骚动。罗普斯说:“这个词似乎与我们所谓‘无政府状态’有着某种不好的联系。”[111]路加福音21:9用它来描述parousia(译注:主再来的日子)到来之前的骚乱、暴动和反叛。这种“智慧”没有带来和谐,反而造成纷争和无序;没有带来更亲密的团契,反而破坏了彼此的关系。这样的“智慧”绝不可能出自于神。
它在本质上是各样的恶行的根源。行(pragma)也许表示行为或发生的事情,本身并不带有任何道德属性;这个词可以更一般地表示“事物、事情、事件”。这里的形容词恶(phaulon),则表明了上述事件或情势的道德特征。它所孕育的恶,不是出于“主动或被动的恶意或恶行”,而是来自于“它毫无益处,从它里面不可能得出任何真正的价值”。[112]但是在新约中,这个词通常用来表示与善相对的某种道德含义。“在道德领域中,”罗伯逊观察到,“单纯的漠不关心很快就会变成恶。”[113]这个名词和形容词的组合,也许可以优雅地翻译为“一切卑劣之事”(every vile thing,新美国标准圣经),将一切形式的恶都包括在内。鉴于这种“智慧”没有任何道德或属灵价值,它绝不可能是神的仁慈赏赐(1:17)。
3.真智慧掌权的证据(17-18节)
利用转折连词但是(de),雅各现在开始用高超的技巧来刻画神所赐下的智慧之特征(17节)和果子(18节)。[114]
(1)真智慧的特征(17节)
不像前面所揭发的虚假“智慧”,这种智慧来自于神。在第15节里,雅各断定智慧是从上头来的,只不过虚假的智慧还不够格。现在,他不再重复完整的“从天降下来的”(anōthen katerchomenē),而是简单地使用了副词anōthen,字面意思是“从上”,强调了这种智慧的基本属性。以下所列的各项特征,都属于这种“从上头来的智慧”(hē anōthen sophia)。
雅各一共列举了七种特征,其中一种具有双重元素。这种智慧先是清洁,后是热爱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和善果,不偏不倚,真诚无伪。佐德易阿特斯指出:“雅各使用这些形容词来描述从天而来的智慧,而不是人自以为有的智慧。”[115]
天上的智慧先是清洁,突出表明了这种属天智慧的本质。它最重要的性质是“清洁”,纯净无污,不沾一点恶,与嫉妒纷争都无关涉。它带有“纤尘不染、对一点污物都会极其敏感”的意思。[116]亚当森说,这个词“在七十士译本和新约中都很少使用。在这里,它不仅描述一种礼仪上或身体接触上的纯净无污,而且还有一种真诚的道德和属灵正直之意……特别与基督有关,就像约翰一书3:3所描述的一样”。[117]基督在品格上,是所有信徒的道德楷模。这个美德列在首位,不是因为它在时间上第一个出现,而是因为它最重要。它是接下来所有品格的源头和关键。
后是热爱和平,列出了智慧从内在清洁所发出的第一个外部品质。从天而来的智慧“为和平做好了准备”[118],通过控制不和、调解纷争而争取和平、养育和平。它促进“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的正确关系”。[119]但它绝不以牺牲清洁为代价来追求和平。它不会为了维持和平而与罪妥协。但是即使在与罪斗争时,它也渴望和平,希望通过智慧的劝告,弥合所有的分歧。
温良(epiekēs)是一个不容易翻译成英文的形容词。巴克利把它称为整个美德列表中“最不可翻译的”词汇。[120]除了通常的“温柔”之意,我们的英文译本将其翻译为各种各样:“温良”(considerate,新英文圣经、新国际译本、古德斯皮德译本),“克制”(forbearing,莫法特译本),“殷勤”(courteous,当代语言圣经、韦茅斯译本),“通情达理”(reasonable,罗瑟拉姆译本、斯科菲尔德译本),以及“亲切”(kindly,耶路撒冷译本)。它表达了尊重他人、愿意在对待他人时采用较不严厉的态度之意。伯迪克说,在七十士译本中这个形容词“大多数情况下用在神对君王的处置上。尽管他有充分的理由严厉地惩罚人的罪,却选择了温柔良善的处理方式。神的百姓也应当具备这种属神的品格”。[121]马太福音18:24-30,耶稣在讲述一个仆人被主人免去了许多的债,却无情而严酷地对待欠他很少钱的同伴时,描述了与此相反的特征。诺林提出,可以将这个词翻译为“温柔的通情达理”,这样可以同时表达温柔和公平之意。[122]
柔顺(eupeithēs)一词,在新约中仅见于此,从词源学上分析其含义是“容易被说服,引申为愿意考虑别人的理由、愿意听取人的意见”。[123]这是一种柔和的态度,随时预备采纳更好的方法;它与固执不认错正好相反。正如莫所说,这种智慧是“‘容易被说服的’——并不是软弱、轻信或容易上当,而是在不涉及根本的神学或道德原则时,乐于尊重他人的意见”。[124]
满有怜悯和善果,是这个美德列表中唯一的双重元素,与第16节“各样的恶行”针锋相对。怜悯并不仅仅是可怜别人的感觉;它是同情他人、因而愿意给予帮助的态度。怜悯不是根据那可怜之人是否配得,而是宁愿根据那人的需要来行事。这是神自身所持有的态度(诗86:5,100:5,103:8;弗2:4),因为他喜爱怜悯胜过审判。神希望人类彼此以怜悯相待,也嘉许这样的做法(赛58:6;何6:6;弥6:8;太23:23;路10:37)。形容词满有,强调了天国智慧之特点是充满了怜悯。这样的人生也将会满有善果(karpōn agathōn)。佐德易阿特斯说:“雅各在这里所用‘果子’一词,表明他期待我们通过怜悯的言语和行为,结出果子。”[125]形容词善指的是这些果子良善的性质,而复数名词则表明所结出的果子各种各样。各种怜悯的行为,将会丰富地收获各种各样的果子。
最后,雅各用两个否定性特征结束了对天国智慧的描绘。不偏不倚(adiakritos)译自一个意义不甚明确的形容词。这个形容词在新约中仅见于此。它来自常见的动词diakrinō,基本含义是“分裂”;加上字母alpha为前缀,表示否定之意。如果用动词的被动含义,这个形容词就表示“没有被分裂”,表明这智慧没有分歧或不和睦之处,于是可以引申为坚固的、不动摇的意思。在1:6里,雅各曾经使用过这个动词的主动形式。若是如此,其含义就是智慧在行事上是一致的;它并不根据不同的场合而选择不同的立场。这种行事的方式,与第9-12节所描写的不受控制的舌头之善变,形成了直接的对立。“没有分歧”(美国标准译本)这种译法,似乎就是想要表达这样的含义。其他现代译本的译法花样繁多,比如“不动摇”(新美国标准圣经),“没有不确定性”(修订标准译本),“毫不踌躇”(韦茅斯译本),以及“直截了当”(新英文圣经)。但是,如果这个来自动词的形容词采取主动的含义(“制造差异”),那么它就带有“不偏不倚”(新国际译本)或者“没有偏袒”(英王钦定本、蒙哥马利译本、罗瑟拉姆译本)之意。在2:4里,这个动词大概采取的这种含义。于是,它的教训就是:天国的智慧没有偏见,与雅各业已定罪的“智慧”不同。米顿赞成这种观点,因为它“符合我们对雅各的认知”。[126]然而,上述两种含义都有可能。显然,这种智慧“在心里是一致的”[127],不会造成分裂或不和。
真诚无伪(anupokritos),字面意思是“没有假冒为善”,表明这种智慧没有任何虚伪;它不需要带着面具行事,因为它没有任何需要掩盖之处。当智慧总是采取直截了当的立场时,它不需要任何虚伪的掩饰。从积极的方面看,这意味着智慧是“真诚的”,完全诚实。
(2)真智慧的果子(18节)
在和平中撒种的、使人和平之人,要获得义的丰收。在最后的结论中,雅各用了连词de,但新国际译本没有译出。它表明作者还有更多的话要说,但他并没有对真智慧进行进一步的描述,而是补充说明了它将带来的后果,完成了整个讨论。雅各在结束讨论的时候,“没有简单地将‘和平’当作智慧众多品质之一列出,而是提到了‘使人和平’”。[128]
新国际译本为了让翻译更为清晰,颠倒了原文略显重复的语序。这一节按照严格的字面意思翻译,应当是“现在(那)公义的果子在和平中要被栽种——被那使人和平的”。这个句子的主语是“公义的果子”(karpos dikaiosunēs)。两个动词都没有冠词,清楚地表明雅各要讨论的是果子的品质。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来理解这句话。属格的“公义的”三个字可以视为同位语,表示所结的果子就是公义;或者可以理解为主词所有格,表示公义结出的果子。为了支持前一种观点,诺林指出,在阿摩斯书5:7中“公义的果子”与“茵陈”(苦涩)相对。[129]米顿也觉得从上下文来看这种观点更合理。[130]但是其他人从以赛亚书32:17明确给出的公义与平安之关系,为主词所有格找到了清楚的支持证据[131];同时,通过类比路加福音3:8(“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以弗所书5:9(“光明〔所结〕的果子”,美国标准译本),以及加拉太书5:22(“圣灵〔所结〕的果子”),也更倾向于这种解释。在前一种观点中,公义作为敬虔生活的特征,自身就是它所结出的果子。在后一种观点中,公义之中蕴含着可以栽种的种子,能够收获的同类的果子。从实用角度看,这两种解释的含义相同,但后一种解释似乎更好一点。
说这种果子是在和平中撒种的,是一种不同寻常的说法;我们一般会想到撒下的种子,而不是果子。但是这句话暗示,当种子撒下的时候,撒种之人就开始对收获满怀期待。人们现在也用播种作物这样的说法。这里动词的现在时态标志着习惯性的做法;被动语态没有明确地给出撒种者的身份,但显然他是一位使人和平的人,也是一位义人。正如戴维斯所说:“在使徒行传第15章和第21章里,路加把雅各刻画为一位使人和平的人,但是他的教导并不是来自于自己的偏好,而是根据耶稣的话语‘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太5:9)。”[132]“在和平中”这个短语被放在动词之前,强调了撒种所需要的环境因素。在这里,“和平”是从人的视角来看待的,指向真智慧所产生的和谐关系。在分裂和争执中我们无法有效地建立公义。
使人和平之人(tois poiousin eirēnēn),既可以表示“向那些使人和平的人”(间接受格),也可以表示“由那些使人和平的人”(工具受格)。也许雅各在组织句子的时候为了让两种含义都说得通,故意去掉了限制性前置词。公义的果子不仅要由使人和平的人来撒种,而且他们也能享受自己辛劳的结果。“整个过程的开始、发展和结束都在和平之中。”[133]
“使人和平之人”表明了撒种者主要的行动特征;他们如此行事并不需要任何官方的头衔或地位。他们自己就是和平,但是同时也用行动促进与其他人的和平关系。受到天国智慧的激励,他们希望弥合纷争,让人们彼此恢复兄弟一样的和平关系。与此同时,他们也享受了自己竭力促进的和平和团契关系所带来的祝福。
[1] J. Ronald Blue, "James," in The Bible Knowledge Commentary, New Testament, p. 827.
[2] Simon J. Kistemaker, New Testament Commentary, Exposition of the Epistle of James and the Epistles of John, p. 106.
[3] James A. Kleist and Joseph L. Lilly, The New Testament Rendered from the Original Greek with Explanatory Notes.
[4] 旧的英文版本译为masters(英王钦定本),表示“学校老师”(schoolmaster)的意思,但是容易被误解(译注:现代英文中master有‘主人’的意思)。这个词指的是师生关系,而不是主仆关系。
[5] Sophie Laws, A Commentary on The Epistle of James, p. 141.
[6] James Hardy Ropes, A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Epistle of St. James, The International Critical Commentary on the Holy Scriptures of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p. 227.
[7] Harold S. Songer, "James," in The Broadman Bible Commentary, 12:120.
[8] James Moffatt, The General Epistles, James, Peter, and Judas, The Moffatt New Testament Commentary, p. 47.
[9] Eidotes 是一个古老的完成时态词形,但是这里用作现在时态。
[10] E. H. Plumptre, The General Epistle of St. James, The Cambridge Bible for Schools and Colleges, p. 78.
[11] E. C. Blackman, The Epistle of James, Torch Bible Commentaries, p. 108.
[12] E. G. Punchard, "The General Epistle of James," in Ellicott's Commentary on the Whole Bible, 8:368.
[13] Spiros Zodhiates, The Labor of Love, p. 78.
[14] 英王钦定本的翻译”n many things we offend all”,不应当被误解为“在许多事情上我们冒犯了所有人”。
[15] R C. H. Lenski,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Epistle to the Hebrews and of the Epistle of James, p. 610.
[16] Jospeh Bryant Rotherham, The Emphasized New Testament.
[17] Theordore H. Epp, James, the Epistle of Applied Christianity, p. 155.
[18] Lenski, p. 610.
[19] Rudolf Stier, The Epistle of St. James, p. 367.
[20] Frank E. Gaebelein, The Practical Epistle of James, p. 77.
[21] Robert Johnstone, Lectures Exegetical and Practical on the Epistle of James, p. 238.
[22] Laws, p. 145.
[23] William Barclay, The Letters of James and Peter, The Daily Study Bible, p. 99.
[24] 英王钦定本根据公认经文的idou,翻译为“看哪!”(Behold),但这种异文仅出现在少数几种晚期的抄本中。各种抄本,或作ei de(“如果现在”),或作ide(“看哪!”)。但是鉴于圣经抄本常常搞混ei和i,也许抄写员想要写ei de,却写成了ide。现代文本批评专家认为原文更可能是ei de——这个短语最好地解释了各种抄本中的异文,并且在语法上更难出现(译注:在文本批评中,编辑们倾向于语法上更难解释的异文,因为抄写员较不可能将简单的异文改写为难解的异文)。公认经文将ide改为人们更熟悉的idou。有关证据,见联合圣经公会希腊文新约圣经第3版、奈瑟勒-阿兰德新约希腊文圣经第26版。
[25] Zodhiates, pp. 94-95.
[26] Stier, p. 370.
[27] 同上。
[28] E. M. Blaiklock, "Ships," in The Zondervan Pictorial Encyclopedia of the Bible, 5:414.
[29] 按照新约通常的用法,这里的最高级形容词带有绝对最高级的意思,表示“非常”、“特别”等意。见H. E. Dana and Julius R Mantey, A Manual Grammar of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p. 121.
[30] Bo Reicke, "The Epistle of James, Peter, and Jude," in The Anchor Bible, 37:37-38.
[31] Johnstone, p. 249.
[32] Alfred Plummer, "The General Epistles of St. James and St. Jude," in An Exposition of the Bible, 6:597.
[33] Zodhiates, p. 104.
[34] Joseph B. Mayor, The Epistle of St. James.The Greek Text with Introduction, Notes and Comments, p. 108.
[35] Douglas J. Moo, The Letter of James, p. 123.
[36] 公认经文在这里选用了“小”(oligon),但是这种异文缺乏足够的抄本证据支持。
[37] Henry Alford, The Greek Testament, vol. 4, pt. 1, p. 304.
[38] L. E. Elliott-Binns, "The Meaning of Hulē in Jas. III.5," New Testament Studies 2, no. 1 (September 1955): 48-50.
[39] Ralph P. Martin, James,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p. 113.
[40] Eric F. F. Bishop, Apostles of Palestine, p. 186.
[41] Stier, p. 372.
[42] Lenski, p. 615.
[43] 见Ropes, p. 234; Burton Scott Easton and Gordon Poteat, "The Epistle of James," in The Interpreter's Bible, 12:47; Martin Dibelius, 'James.A Commentary on the Epistle of James," in Hermeneia—A Critical and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e Bible, pp. 194-95 and n.69; Martin, pp. ll3-15; James B. Adamson, The Epistle of James, pp. 158-64。
[44] F. Blass and A Debrunner, A Greek Grammar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Other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 p. 143.
[45] Edwin T. Winkler, "Commentary on the Epistle of James," in An American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p. 47.
[46] Dibelius, pp. 193-94 and n. 65.
[47] Kleist and Lilly.
[48] Zodhiates, p. 109.
[49] Blackman, p. 110.
[50] Mayor, p. 111.
[51] R. J. Knowling, The Epistle of St. James, Westminster Commentaries, p. 75.
[52] Plummer, 6:598.
[53] J. N. Darby, The "Holy Scriptures," A New Translation from the Original Languages.
[54] Winkler, p. 47.
[55] Dibelius, pp. 196-98.
[56] Lenski, p. 618.
[57] Blue, p. 828.
[58] J. W. Roberts, A Commentary on the General Epistle of James, p. 131.
[59] R. E. Davies, "Gehenna," in The Zonderoan Pictorial Encyclopedia of the Bible, 2:670-72.
[60] 马太福音5:22、29、30,10:28,18:9,23:15、33;马可福音9:43、45、47;路加福音12:5。
[61] John Peter Lange and J. J. Van Oosterzee, "The Epistle General of James," in Langes's Commentary on the Holy Scriptures, 23:97.
[62] Kistemaker, p. 112.
[63] R. V. G. Tasker, The General Epistle of James, p. 77.
[64] Roy R. Roberts, The Game of Life, Studies in James, p. 92.(强调字体为作者所加。)
[65] Johnstone, p. 260.
[66] 另外,修订标准译本、贝克译本、罗瑟拉姆译本、韦茅斯译本和当代语言圣经也采用这种译法。
[67] Alexander Maclaren, "Hebrews Chaps.VII to End, Epistle of James," in Expositions of Holy Scripture, p. 435.
[68] 转引自Winkler, p. 48。
[69] Peter H. Davids, The Epistle of James, p. 145.
[70] 希腊文用定冠词“那”来指明具有上述特征的特定的神。新国际译本添加了“我们的”一词,表达了我们与神之间有着个人的联系。
[71] 英王钦定本根据公认经文,翻译为“神,甚至是我们的父”。这种异文缺少文本证据,可能是抄写员篡改了这一不常见的名称。
[72] Richard Wolff, General Epistles of James and Jude, Contemporary Commentaries, p. 60.
[73] Zodhiates, p. 120.
[74] W. E. Oesterley, "The General Epistle of James," in The Expositor's Greek Testament, 4:454.
[75] John Albert Bengel, New Testament Word Studies, 2:454.
[76] Stier, p. 377.(强调字体为作者所加。)
[77] Martin, pp. 119-20.
[78] Knowling, p. 81.
[79] H. Maynard Smith, The Epistle of S. James. Lectures, p. 188.
[80] Moo, p. 130.
[81] 抄本证据在这里显出不同的异文。公认经文的文本是“所以,同样没有盐泉”(so no salt spring also,houtōs oudemia pēgē halukon kai)。Houtōs(“同样”)一词不见于早期的抄本和几个重要的版本,但在许多抄本中都有这个词。文本批评家们一般认为,抄写员更可能增加了这个词,而不是从原稿中删除了它;为了让整个画面显得完整,似乎自然应当增加这个词。尽管我们不能完全确定原文,但对于文义并无实质性影响。有关证据,见联合圣经公会希腊文新约圣经第3版。
[82] Knowling, p. 83.
[83] Zodhiates, p. 132.
[84] Dibelius, p. 207.
[85] Easton and Poteat, p. 50; Joh. Ed. Huther,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Handbook on the General Epistles of James, Peter, John, and Jude, p. 119.
[86] C. Leslie Mitton, The Epistle of James, p. 134.
[87] Blackman, p. 120.
[88] Arthur Carr, "The General Epistle of St. James," in Cambridge Greek Testament, p. 47.
[89] 当前辈们翻译英王钦定本时,以conversation一词精确地反映了希腊文的含义,因为那时这个词表示一个人的社交行为。现在,这个词的意思变成“谈话”,因此这种翻译容易让人误解。见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2:546。
[90] Peter H. Davids, James, New International Biblical Commentary, p. 88.
[91] Moo, p. 132.
[92] 第一类条件句,暗示实际发生的情况。见A. T. Robertson and W. Hersey Davis, A New Short Grammar of the Greek Testament, p. 350。
[93] Lange and Van Oosterzee, p. 100.
[94] 以及修订标准译本、新美国标准圣经、当代语言圣经、新英文圣经、贝克译本、克莱斯特-利利译本、莫法特译本、蒙哥马利译本、罗瑟拉姆译本以及威廉姆斯译本。见“参考书目”。
[95] William F. Arndt and F. Wilbur Gingrich, A Greek-English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Other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 p. 309.
[96] 在哥林多后书12:20和加拉太书5:20里所用的复数形式,表示“因自私而发怒”或“纷争”之意。
[97] Ropes, p. 246.
[98] Knowling, p. 86.
[99] Oesterley, p. 455.
[100] Rudolf Bultmann, "Katakauchaomai," in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3:653.
[101] Zodhiates, p. 160.
[102] Dibelius, p. 210.
[103] Mayor, p. 123.
[104] 古德斯皮德译本和利利译本实际上与此相同。
[105] Davids, The Epistle of James, p. 151.
[106] Harold S. Songer, "James," in The Broadman Bible Commentary, 12:125.
[107] Davids, James, New International Biblical Commentary, p. 89.
[108] Arndt and Gingrich, p. 902.
[109] 英王钦定本翻译为devils,1881年的修订译本(Revised Version)也加以保留,是一个不幸的误译。
[110] Dibelius, p. 212.
[111] Ropes, p. 248.
[112] Richard Chenevix Trench, Synonyms of the New Testament, p. 317.
[113] A. T. Robertson, Practic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ristianity.The Wisdom of James, p. 182.
[114] 学者们对作者用希腊文给出一连串美德的技巧给与了高度评价。见Adamson, The Epistle of James, p. 154; Martin, p. 133。
[115] Zodhiates, p. 174.
[116] Brooke Foss Westcott, The Epistles of St. John, The Greek Text, p. 101.
[117] Adamson, p. 154.
[118] Werner Forester, "Eipenikos," in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2:419.
[119] William Barclay, The Letters of James and Peter, The Daily Study Bible, p. 111.
[120] 同上,p. 112。
[121] Donald W Burdick, "James," in The 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 12:191.
[122] Knowling, p. 89.
[123] Johannes P. Louw and Eugene A. Nida, Greek-English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Based on Semantic Domains, 1:423.
[124] Moo, p. 136.
[125] Zodhiates, p. 201.
[126] Mitton, p. 141.
[127] Adamson, p. 156.
[128] Laws, p. 165.
[129] Knowling, p. 91.
[130] Mitton, p. 143.
[131] Ropes, pp. 250-51.
[132] Davids, James, New International Biblical Commentary, p. 91.
[133] Plummer, 6: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