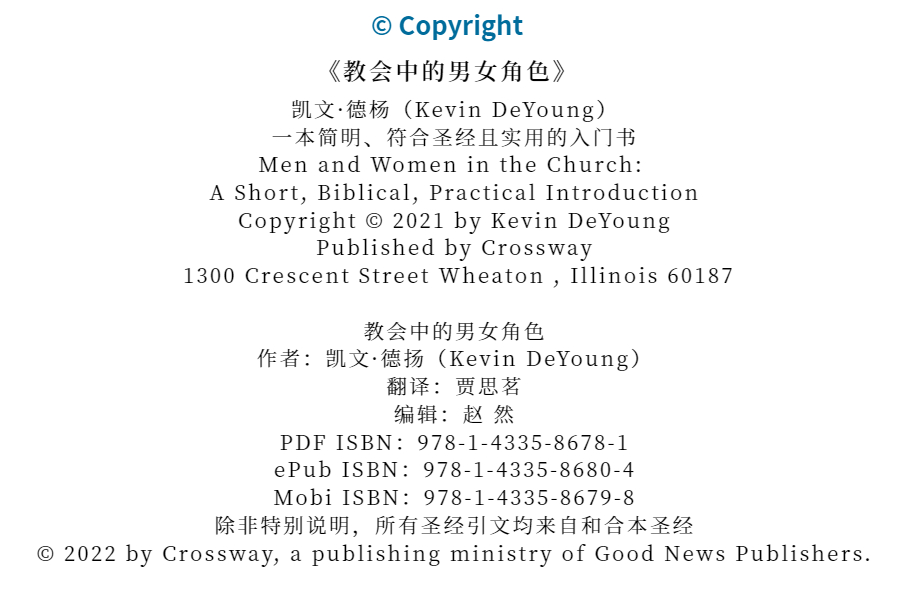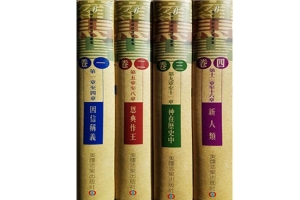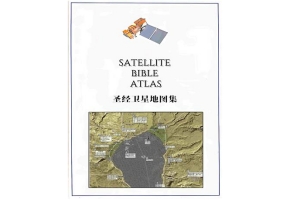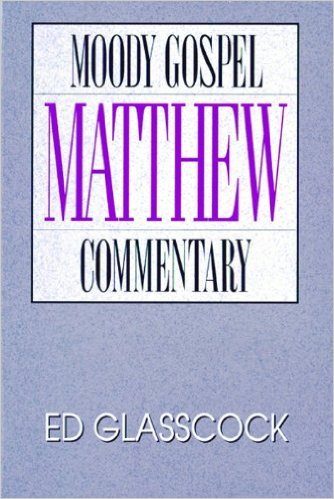主张互补主义的教会是否应当允许女性在主日讲道?
假设你认同本书中那些圣经和神学上的论证,你也在《创世记》和耶稣那里看到了与这些论证相符的模式,也这样来解读保罗的教导,关于在家中和教会中男性的领导力你也得出了和本书一样的结论,并且你也不支持女性被按立,认为自己教会中的长老和牧师都应当是男性。但你却可能依旧不能确定,女性是否可以偶尔在主日早上讲道。我有一些朋友,认同这段话中上述所有的结论,但却相信女性在长老的权柄下讲道并不违反基本的互补主义信念。这个结论是如何得出的?我为什么认为该结论大错特错?这正是这篇附录要谈论的要点。
我所见过的支持女性讲道的最佳论证,是澳大利亚牧师兼护教学家约翰·迪克森(John Dickson)在其著作《倾听她的声音:圣经邀请女性讲道》(Hearing Her Voice: A Biblical Invitation for Women to Preach)中所提出来的。[1]巴刻(J. I. Packer)、克雷格·布鲁姆伯格(Craig Blomberg)、格拉厄姆·科尔(Graham Cole)、莱特(Chris Wright)都为这本书写了推荐语,由此可见这是一本很有影响力的书。迪克森的这本书是清晰易懂的典范。在一百零几页的篇幅中,承认自己是“广义互补主义者”(第88页)的迪克森,深思熟虑、直截了当地为女性在主日崇拜中讲道的正统性作了辩护。
毫不意外,迪克森所专注的经文是《提摩太前书》二章2节。尽管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认为这处经文的应用是显而易见的——女性不被允许教导或使用权柄,因此她们不应当讲道——但迪克森却认为我们误解了保罗所说的“教导”的意思。迪克森写道:“简单来说,新约提到了许多种通过公开讲话而进行的事工——教导、劝勉、传讲福音、说预言、宣读经文等——而保罗认为只有其中一种事工专属于够资格的男性:‘教导’”(11-12页)。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简单的三段论来总结迪克森的论证核心:女性在崇拜中唯一不能做的事就是教导。在保罗看来,教导被构想成了一种专门的、狭义的事工,不同于我们现代的讲道。因此,女性在教会崇拜中几乎能以所有的方式讲话,包括讲道。
如果讲道不算教导,那么保罗所说的“教导”又是什么意思呢?迪克森解释道:
《提摩太前书》二章 12 节所指的并非一种以圣经为基础的一般讲话类型,而是指贯穿于新约的一种特殊活动,即保存并传承使徒们传下来的传统。这种活动不同于我们在今天典型的释经性讲道中所看到的对圣经经文的解释和应用(第 12 页)。
迪克森分四部分对这一初步得出的结论进行了论证。
第一部分 圣经提到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宣讲:说预言、传讲福音、宣读经文、劝勉、教导等等。通过诸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28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罗马书》十二章4至8节以及《提摩太前书》四章13节这些经文,我们了解到,保罗并不认为这些事工都是一样的。这些类型的讲话当中只有一种——就是教导活动——是专属于男性的(第27页)。
第二部分 在古代社会,尤其在保罗看来,教导(didasko)是一个专门用来指“传达一种固定的口述传统”的词(第34、45页)。教导并不是指说明或解释,而是指完整地传达话语(第33页)。随着圣经正典的完成,这种专门意义上的教导也就不再需要了。
第三部分 在新约中,教导的意思从来都不是解释或应用某处经文(第50、54页)。教师是一个将固定的传统或使徒的话语从最初的源头传达给新信徒群体的人(第57、59、61页)。一些现代的讲道可能包含了这种传达的元素,但这并不是每周解经式讲道的典型功能(第64页)。我们所认为的那种讲道,其实被称作“劝勉”更恰当(第65页)。
第四部分 如今我们在新约中就能看到使徒的信息。再没有任何人需要负责保存和传达有关耶稣的固定口述传统了(第72、74页)。如今的讲道者们或许类似于古代的教师,但我们不会像他们那样以同样的程度、方式或权威来保存和传达使徒的信息(第73、75页)。在典型的讲道中,讲道者会解释使徒们的教导,劝勉我们听从并运用这些教导,这个过程本身其实并不是教导。现代的讲道更像是说预言或劝勉(视你自己的定义而定),二者对女性来说都是开放的(第75页)。
过于狭隘的理解
迪克森在论证的同时作了一些学术性的脚注,也一直在作出说明和限定。但他的论证有着十分清楚的主旨:圣经中的“教导”并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的讲道。唯有教导对女性而言是禁止的。因此,女性可以在教会中讲道。
我之所以认为迪克森的论点不可信是出于两个基本的原因。我认为他对古代教导的看法太狭隘,对现代讲道的看法又太浅薄。[2]我要通过几个不同的角度来查看教导,从而剖析一下这个结论。
初代教会中的教导
迪克森论证方式中的长处是,他正确地指出了新约中几个表示“讲话”的不同的词。的确,教导、劝勉、说预言、宣读经文是不一样的。然而他对“教导”过度严格的定义与我们所看到的证据不符,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与基本常识不符。如果“我不许女人教导”的意思是“我允许女性讲道,因为讲道并不涉及教导”,那么我们必定是在运用“讲道”和“教导”这两个词十分有限的定义。
更重要的是,如果这种十分微妙的解读成立,那么为何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几乎所有的解经家都没有注意到呢?迪克森在自己著作的最后一页,一个透露些许真相的脚注中承认:
我很肯定,在初代教会的一段时期内,“教导”一词指的是解释和应用新约(以及整部圣经)中书写成文的话语。这将是一个有趣的研究方向,但我不确定这是否能推翻《提摩太前书》二章 12 节中,保罗是在另一种意思上使用这个词的相关证据。(第 104页)
这是一个坦诚的真相。但它引发了一个问题:“如果‘教导'在古代社会显然有‘重复口述传统'这种狭隘的意思,那么为何似乎没有人熟知这种独有的专门定义呢?”圣经当然是我们的最终权威,但当某种论证十分依赖于公元一世纪的背景时,我们应当认为教会最初几个世纪的情形应该增强而非削弱这种论证。
我们可以以《十二使徒遗训》(Didache)为例。[3]这份公元一世纪末的文献对教师有诸多的谈论。教师应当“教导所有之前被提到的事”(就是此文献头十章中提到的事)(11:1)。教师应当教导与《十二使徒遗训》所规定的教会秩序相符的事(11:2)。重要的是,《十二使徒遗训》承认存在着一群四处游历的教师、使徒、先知,并且说他们都在教导(didaskon)(11:10-11)。这一点就表明“教导”这个词广泛得足以包括先知和其他讲话人所做的事,更别说《十二使徒遗训》本身了。
“教导”当然可以包括传达有关耶稣的口述传统,但却不能仅限于此。正如休斯·奥利潘特·欧德(Hughes Oliphant Old)的解释:“《十二使徒遗训》认为存在着一群数量庞大的先知、教师、主教(bishops)以及执事,他们全职讲道和教导。”[4]有了一群全职教师以及“一群每日聚会、听道的圣教会中的男女角色徒”,[5]我们很难想象这些参与“教导”的各类圣职人员始终坚决不对任何经文作出解释。
当然,真正的教师的确一直在传达使徒们的信息,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只是在简单地重复耶稣的话语。《十二使徒遗训》告诉父母要教导(didaxeis)儿女敬畏神(4:9)。作者(们)显然并不认为这里的“教导”被局限于十分严格的定义,也不认为讲道不过是对经文连续的解释外加应用。“我的孩子,你要记念那昼夜向你传讲神话语的人,尊重他如同尊重主。因为在哪里传讲主的性情,主就在那里。”(4:1)根据《十二使徒遗训》,教导不只是传达口述传统,讲道也不只是说几句劝勉的话。
犹太会堂中的教导
迪克森论证当中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保罗对教导的观念扎根于法利赛人的惯例:他们传达着先祖们的口述传统(可7:7)。正如法利赛人可能会不断重复希勒尔(Hillel)的语录[6],新约教师们也可能会不断重复耶稣的语录。按照迪克森的观点,与新约“教导”最相似的行为就是传达《密西拿》(Mishnah)[7]中重复和积累下来的拉比传统。(第39页)
这在迪克森看来是一条重要的推理路线,他反复提到过该路线(第39、73、100-102页)。这种论证的问题是双重的。
首先,《密西拿》虽收集了公元一、二世纪拉比们的语录,但这些拉比认为自己是在解释和应用摩西五经(Torah)。也就是说,即便《密西拿》是有关“教导”的一个例子,但“口述传统”和“经文解释”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线。
其次,与《密西拿》相比,犹太会堂的崇拜更类似于早期的基督教崇拜。毕竟,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中谈到的是共同敬拜(corporate worship)。在基督教时代之前的许多个世纪里,犹太人培养出了讲道的技巧,并在会堂崇拜中赋予其享有特权的地位。欧德认为:“有一大群核心的全职人员,他们终生研究圣经,也时刻预备着当受到会堂领袖的邀请时站出来讲道。”[8]这使我们可以更合理地认为,当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二章12节中禁止女性教导时,想到的是一种与仅仅重复口述传统相反、发展成熟的传统:一些人在犹太教的崇拜中解释经文。
旧约中的教导
另外,这种会堂中的教导事工起源于旧约。摩西曾教导以色列民神的律例典章——的确重复了它们,但也解释和应用了它们(申4:1-14)。第5节中“教导/教训”一词在一世纪使用的希伯来圣经希腊文译本《七十士译本》(LXX)中被译成了希腊文单词didaskō。祭司们,或者说至少有一些祭司需要去教导祭司(代下15:3),并走遍犹大各城教导(edidaskon,《七十士译本》)百姓律法书(代下17:9)。以斯拉立定心志研究耶和华的律法,又在以色列教导(diaskein,《七十士译本》)耶和华的律例典章(拉7:10)。同样,以斯拉和利未人念神的律法书,又教导(edidasken,《七十士译本》)百姓,使百姓明白他们所念的(尼8:8)。
《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所描述的这些惯例充分表明,这些惯例在当时已完全地被建立起来了。有经文,有教师,有会众。我们看到了犹太教会堂崇拜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基督教崇拜当中所有最基本要素的缩小版。我们很难想象保罗是想要表达这一点(更别说他的听众们能理解这一点了):当保罗谈到“教导”时,他完全没有想到旧约或犹太教传统,而只是想到了法利赛人传达的口述语录。在上述旧约中的每个例子中,教师都解释了一处书写成文的经文。这并不意味着didaskō(“教导”)必然涉及到了经文解释,但那些认为绝不可能有这种意味的人必须拿出证据来。
新约中的教导
我认同迪克森的这种看法:我们不应当在尽可能最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提摩太前书》二章12节中的“禁止女性教导”。保罗并不是想禁止女性将知识传达给他人。他是在谈论崇拜中的恰当做法,而不是我们在《提多书》二章中所看到的那种女性对女性的教导,也不是《使徒行传》十八章中百基拉和亚居拉对亚波罗的教导。虽然我们拒绝“教导”最宽泛的意义,但却并不能因此就意味着最狭隘的意义是唯一的替代选项。迪克森想要我们将“教导”等同于传达口述传统。后者当然是使徒时代教义的一部分,但新约中许多谈到使徒传统的地方都从未提到过didaskō(“教导”)(林前2:2,3:10,11:2、23-26,15:1-11;加1:6-9;帖前4:1-2),而是用“领受”、“传”或“传给”这类的表述。
至关重要的是,登山宝训被称作“教训/教导”(太7:28-29)。迪克森认为,登山宝训是“教训/教导”,这是因为耶稣当时是在纠正文士们的传统并传达他自己的权威传统。耶稣并没有做解释经文的事(第54页)。迪克森的确说对了耶稣当时正在做的事。然而,他却错误地宣称了耶稣当时没有做的事。
登山宝训充满了旧约引喻(allusion)、类比(parallel)以及解释。我们并非必须认为耶稣是在作一次现代意义上的讲道。要点不在于新约中的每一处“教导”都表示“解释”,而在于这两个概念不能完全被分开。
公元一世纪犹太教对“教导”的理解必然与“正确解释神所默示的经文”不可分割。许多人称耶稣为“拉比”,这是一个表示“教师”的非正式头衔。耶稣作为一名教师,时常引用或解释旧约圣经。事实上,欧德认为耶稣在圣殿中的教导将耶稣在地上的服侍推向了终点,这是为表明耶稣履行了拉比的职责。在《马太福音》二十一至二十三章中,我们看到当时各种不同派别的人——希律党人、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带着有关律法的问题来见耶稣,耶稣都一一作了回答。[9]在解决他们的谜题、化解他们的圈套时,耶稣展示出自己是教师中的教师,拉比中的拉比。而在这一展示的过程中,他始终在解释和讲解圣经。公元一世纪犹太教对“教导”的理解必然与“正确解释神所默示的经文”不可分割,但也不应局限于“传达口述传统”。
教牧书信中的教导
尽管有上述的旧约背景、犹太会堂背景、登山宝训中“教导/教训”的用法以及对初代教会中的“教师”更宽泛的理解,但假如保罗在教牧书信中选择使用“教导”一词十分狭隘的定义呢?迪克森在查考了教牧书信中“教导”一词的每一处使用后总结说,“教导”无论作为动词还是名词,都不是指经文解释而是指向教会宣告使徒的话语(第59页)。简而言之,“教导”的意思不是解经和应用,而是重复和宣告(第64-65页)。保罗所说的“教导”绝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文解释(“绝不是”是迪克森的原话,我在此作了强调)(第74页)。迪克森认为,其他地方的教导无论涉及到了什么,在保罗看来,都只是指宣布口述传统。
迪克森当然正确地认识到了教牧书信中的“教导”关乎着传达有关耶稣的、美善的使徒真理信息。例如,保守派学者威廉·孟恩思(William Mounce)就完全肯定,《提摩太前书》二章12节关乎着“权威和公开传达有关基督和圣经的传统”,或者说涉及到了“保存和传承基督教传统。”[10]但我们要注意到,孟恩思并没有将基督教传统简化成只有口头言论而不包括经文解释。同样,《新约神学辞典》(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TDNT)也认为,didaskein(“教导”)一词“即便在新约中也与圣经关系密切”。[11]随后,《辞典》又肯定了,即便在教牧书信中“圣经和didaskein之间的历史关联也依旧是完整的。”[12]
这显然是正确的。我们难道会认为,当保罗坚持认为长老能够教导时,这种教导完全不关乎讲解圣经或正确分解真道吗?(提后2:15)教导必定不只是传达口述传统,因为若是那样,保罗怎么可能告诉老年妇人要用“善道”(kalodidaskalos)来指教年轻的妇人呢?或者我们可以想一下《提摩太前书》四章13节,保罗在这里告诉提摩太要公开宣读圣经、劝勉、教导。这些当然都是不同的任务,但按照迪克森的解释,提摩太要宣读圣经,通过圣经来劝勉,然后宣布使徒们说过的信息,而不需要解释。
同样,迪克森认为,当保罗说圣经于教训都是有益的,他的意思是提摩太要私下研读圣经,以便能够更好地被装备来公开地传达使徒的美善信息,但同样不需要去解释经文(第52-53页)。若的确如此,保罗就并没有预想教师们会在督责、使人归正或是教导人学义方面多多解释经文。圣经或许表明了这些任务,但绝未涉及到经文解释(第57页)。这种细微调整过的对“教导”的定义并不能令人信服。让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中的讲道。这里对使徒美善信息的传达几乎没有不涉及到经文解释的。而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中,保罗虽然是在明确地传达他已领受的,但所传的信息并非仅仅重复一套固定的说辞,而是使徒的传统,即照圣经所说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又照圣经所说他第三天复活了。我们无需将didaskō等同于包含三个要点的典型讲道就能看出,传达使徒的信息几乎不可能不涉及到参考和解释经文。
当今讲道中的教导
如果说迪克森对古代教导的定义太狭隘,那么他对现代讲道的理解也太浅薄。按照迪克森的说法,讲道本质上是连续地对经文做出解释外加应用。我承认自己对讲道所涉及的内容有十分不同的看法:我不是认为讲道的范围要小于经文的解释和应用,而是认为不止于此。讲道者对应的希腊文单词是kērux,意思是传道的人(提后1:11)。我们当然不是以使徒所具有的权柄在讲道,但对于那些够资格、蒙召讲道的人,他们的确是在传达使徒的信息,也应当带着权柄讲道。否则保罗又怎会以如此强烈的用语和如此迫切的劝勉吩咐提摩太务要传道,要用百般的忍耐和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提后4:1-2)
最后,我认为迪克森的论证方式不仅在历史和解经方面难以令人信服,在实践上也行不通——至少对互补主义者是这样的。其他人可能会因各种原因支持女性讲道。但一些互补主义者克服重重困难并争辩道:“主日早上的这个信息是分享而不是讲道”或“这种女性讲道是在堂议会(session)的权柄下进行的”,这些人认为,那种任何时候都不允许女性以任何形式讲道的主张似乎太过武断了。
讲道之事——无论是牧师提供了讲台还是长老们给予了遮盖——都不能与使用权柄和参与教导分开,而这两样都是女性在崇拜中不允许做的。
在几处不同的地方,迪克森承认当今的一些讲道可能涉及到了教导,而新约中不同类型的讲话也可能相互重合:
·我并不是说这三种讲话形式(教导、说预言、劝勉)有严格区分,或是在内容和功能上没有任何显著重合。(第24页)
·一些现代的讲道所涉及的内容十分接近于权威地保存和宣布使徒的信息,但我并不认为这是每周宣讲的典型功能。(第64页)
·我并不怀疑提摩太在传达这些使徒的教导时添加了自己的呼吁、解释以及应用,但这些并不是构成或界定教导的要素。每当这种时候,提摩太的行为就会发生转变,更适合被称作“劝勉”。(第65页)
·我并不是在严格地区分教导和劝勉,但我注意到,教导主要关乎着以固定的形式来宣布某些事,而劝勉则主要关乎着激励人顺服和应用神的真理。(第65页)
·毫无疑问,劝勉和说预言当中有一定程度的教导,正如教导中也有某些劝勉(或许还有说预言)。(第66-67页)
·我还认为,每一篇合宜的讲道都传达了某些使徒的信息,只是有一些讲道比另一些传达得更多。(第79页)
当所有这些讲道的要素交织在一起,保罗怎么可能指望提摩太能解开这一团乱麻然后弄清楚不允许女性做的究竟是什么呢?同样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如何辨别一篇讲道什么时候只是不带权威的劝勉,而什么时候又变成了对使徒信息的权威传达?或许我们最好就或多或少地将“教导”视为讲道人在主日所做的事,而不是迪克森所谓高度技术性的“教导”:他将之定义为只有在关联到初代教会、犹太会堂、耶稣的例子或保罗的教训时才有意义。
讲道之事——无论是牧师提供了讲台还是长老们给予了遮盖——都不能与使用权柄和参与教导分开,而这两样都是女性在崇拜中不允许做的。
[1] John Dickson, Hearing Her Voice: A Biblical Invitation for Women to Preach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2014). 在本章中,我参考这本书时都会将具体的页码附在括号里而不是添加一些尾注。
[2] 本章呈现的这些论证最初是我于 2019 年 8 月的博客文章。这篇文章发出不久后,约翰·迪克森回复了一段很长的反驳(http://www.johndickson.org/blog/shouldwomenpreach)。若要逐个梳理他回复中的要点,就超出了本书的谈论范围(恐怕也超出了读者们的期望!)。毫不意外,我的文章没有改变他的想法,他的回复也没有改变我的想法。他的回复有一个重点 :我在他对教导的看法上犯了“稻草人谬误”(即为了反驳而故意曲解了他的论点),忽视了他的坚决主张:圣经的确在保罗的教导观念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这种保罗的解经并不是他教导的主要特征。在本章的结尾处——正如我在最初文章的结尾处一样——我引用了一些出自迪克森的论述,而他在回复中顺着自己的回复又作出了细微的调整。我并不认为自己在理解他的立场时犯了稻草人谬误。更重要的是,我认为自己的批判依旧站得住脚。如果新约中的教导不是由解经“组成”或“定义”的,而是按照迪克森那种微妙的立场,也包含了一些对圣经的反思、解释、应用,那么鉴于保罗禁止女性参与的教导和讲道包含了所有这些要素,女性又怎能被允许讲道呢?
[3] Michael W. Holmes, The Apostolic Fathers: Greek Texts and English Translations, 3rd ed. (Grand Rapids, MI: Baker Academic, 2007).
[4] Hughes Oliphant Old, The Reading and Preaching of the Scriptures in the Worship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vol. 1, The Biblical Period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98), 256.
[5] Old, Reading and Preaching of the Scriptures, 256.
[6] 希勒尔是生活在公元元年前后的一位犹太教领袖和拉比。——译者注
[7] 犹太教的一部律法书,完成于公元三世纪。——译者注
[8] Old, Reading and Preaching of the Scriptures, 102.
[9] Old, Reading and Preaching of the Scriptures, 106.
[10] William D. Mounce, Pastoral Epistles,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Nashville, TN: Thomas Nelson, 2000), 126.
[11]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10 vols., ed. Gerhard Kittel, trans. Gerhard Friedrich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76), 2:146.
[12]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