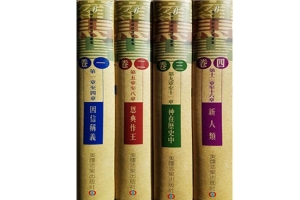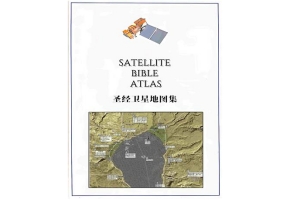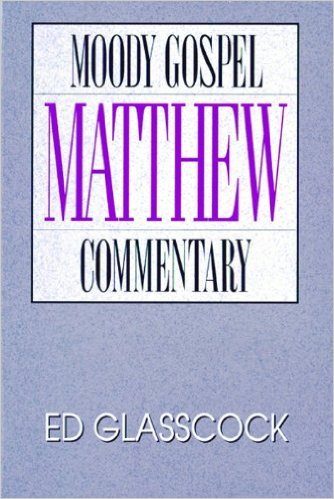第三章 语境分析
解经应该从哪里着手呢?是否应该从最繁琐、最细小的部分开始,由语音、语素、单词,进到短语、从句、句子、段落、篇章,以至整卷书?还是应该按照相反的次序?
良好的解经步骤要求从整个上下文(即“语境”)看细节部分。除非解经者知道经文的思想从哪里开始,以什么形式发展,否则所有琐碎的细节可能就没什么价值。于是,解经最关键的能力就是能够说明一卷书每个大段的概要,以及大段中每个段落的用意。如果解经者在这一点不够强,那么接下来的许多工作都将是浪费时间和精力。
塞缪尔·戴维森(Samuel Davidson)用最直白的话说明了这一点:
在探讨一个大段每个段落之间的关系时……特别需要敏锐与机智。我们也许能说出单个术语的意思,却不能分析连贯的论点。有词语分析能力并不表示有了解释整段经文的能力,这种能力包括四个方面:(a)能找出正确的原因;(b)能找出原本的顺序;(c)能找出对主题确切的描述;(d)能找出不同文体所产生之思想的细微差异。[1]这些能力跟仔细探寻单独术语的各种意思的习惯不同。
因此,问题不仅是常见的那种忘记或忽略紧临的上下文的错误,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种更为严重的错误——企图分割经文,并假定从句、句子(甚至段落)可以有与其上下文无关的独立意思。
解释圣经尤其容易犯这种错误。因为(正确地)相信以语言形式表达的经文信息是神自己借着既自主又顺从的作者想要表达的,许多人就进一步给每个词和从句赋予几乎独立于上下文的意思(复数)。他们不假思索地允许这逐渐演变成以近乎离奇的方式来使用圣经文字,脱离上下文,按自己的喜好来使用——只要是为了属灵的目的,并且跟某处的圣经教训一致就行了。
但是,我们要与这种糟糕的方式划清界限。如果我们所感兴趣的某个真理确实在圣经的另一处有教导,我们就必须立刻从那一处的上下文求取信息。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一处经文的用词正合我意,就假装对它进行注释。这在本质上是故意误导会众,他们会以为我们是将那处经文作为所讨论观点的权威。
不可这样!认识语境既非常必要也非常重要,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四个层次:大段的语境、书卷的语境、正典的语境和紧临的语境。
一、大段的语境
语境(Context)这个词是由拉丁文的con(即“一起”)和textus(即“被编织”)组成,也就是说,当我们提起语境,我们是说到贯穿整个段落的思想上的衔接,也就是把全文编织成一体的那些衔接。
解经者必须体会到,他首要的任务是找出这些像生命之流一样贯穿在各篇大小部分中的思路。如果解释者弄错或忽略了这种衔接关系,他很可能会错失作者借以组织其作品的各部分的范围、结果、目的和整体计划。因此,范围和计划的研究属于语境的研究。
那么,我们怎样进行语境的研究呢?必须要先读一遍这卷书。这样的阅读将是对一些主要的构思和特征的考察。完成这项最初任务的一个方法就是,注意作者有没有在他的序言、结论中,或反复出现的内容中,明确说出他的意图,然后可以有系统地浏览作品的其余部分,以了解这个明确说出的目的或计划是如何体现的。
然而,如果无法确定整篇作品的编排,就要作透视性的研究了。要作这样的研究,解释者必须利用各种线索找出该书大段之间略微显明的衔接之处。例如:
(1)一个重复出现的词、短语、从句或句子,可能会用在每个部分的“开头”(Heading)或每个大段的“结尾”(Colophon)。
(2)常常可能会有文法上的线索,如过渡性的连接词或副词。例如:“于是、因此、所以、但是、虽然如此、这时”和希腊文的οὖν、δέ、καί、τότε、διό等。
(3)一个反问句(Rhetorical Question)可能是一个新主题或大段的衔接点,可能后面又有一连串这样的问题,延续整个大段的论点或计划。
(4)时间、地点或环境的改变,是标明新主题和大段的手法,这在叙事文体中尤为明显。
(5)呼格(Vocative)形式,有意将注意力从一组转到另一组,这是最重要的手法之一,常出现在书信文体中。
(6)动词时态、语态和语气的改变,甚至主语或宾语的改变,可能是开始一个新大段的另一线索。
(7)关键词、观点或概念的重复出现,也可能指出一个大段的范围。
(8)在少数情况下,每个大段的主题会在开头时提出。在那些不寻常的情况下,解释者只需要确保根据作者所陈述的目的来判断这个大段的所有内容。[2]
现在,把一卷书分解成几个主要“运行”的部件,就如同汽车工人把汽车分解成车体、马达、车前杆、电力系统、传动系统、后轮轴等部件,这种打破整体语境似乎很奇怪。但这里的类比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希望发现该卷书是如何“运作”的。从各部分的连接和组织中,我们可以明白它的一贯性和整体功能,就为我们的使用做好了准备。这样,虽然我们的目标是要了解并且能够用一句话(绝对必要时可以用几句话)表达出整卷书的总体主题,但是我们若不对整篇作品作一些初步的检验,就没有办法说出这个总体主题所包含的是什么。
当然,如果作者在其作品的序言或结论直接说出作品的内容,这一步就极大地简化了,我们很容易得知写作的目的。但即使在这种令人愉快的情形下,解释者还是需要确认不同的大段,不过这时有必要了解大段的范围,仅是为了发现作者所说的计划或目的是如何展开的。无论如何,看来最好还是先由分析大段开始,在计划的展开中它直接包含了计划的整体目的和其中的连接关系。
现在,我们提出圣经中一些按照前面所列原则找出大段的分节点的例子,是会有帮助的。
创世记一再重复的短语有着最清楚的轮廓。“某某的后代(或来历)”出现在大段的“开头”有十次之多,每一次都加进一个新的名称,例如“创造天地的来历”(创2:4)、“亚当的后代”(创5:1)、“挪亚的后代”(创6:9)、“挪亚儿子……的后代”(创10:1)、“他拉的后代”(创11:27)等。
但是这种词、短语、从句或句子重复的现象,也可能会出现在大段的“结尾”。马太福音中有五次用“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作一段主要教训结束时的交待(太7:28,11:1,13:53,19:1和26:1)。
同样地,所罗门也用重复的叠句(Refrain)将传道书分为四个大段。他所重复的句子类似这样:“吃喝并享受劳碌所得的,因为这是神的赏赐”(传2:24-26,5:18-20,8:15)。[3]
另外,罗马书6:1用一个反问句导入一个新的大段:“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事实上,在整个大段中保罗都用τί οὖν(“这样,怎么说呢?”罗6:1、15,7:7)来联系。旧约中也有类似重复反问句的情形,伯特利和耶利哥的先知门徒都问以利沙同样的问题:“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傅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每一次他都回答:“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王下2:3、5)这个问题的功用在于推动整个故事的发展,并随着以利亚被接升天的时刻渐渐逼近来结束每一段情节。
以反问句来构建整卷书的例子中,最显著的莫过于玛拉基书了。玛拉基一再以独特的对话风格,大胆地用“从神而来的宣告”开始每一大段,而听众则以装假、无辜、委曲的反问作为回应,问到“我们如何……”“我们在何事上……”也就是希伯来文的בַּמָּה(“在何事上?”玛1:2、6、7,2:14、17,3:8、13)。对于神向以色列所发的每一项指责,他们总是以反问来回应:“是我们吗?不,不是我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解释者若想找出玛拉基书的适当分段点,这些恶劣的态度反倒有帮助。
有时,所重复的是一个带有呼格词的祈使句。这在弥迦书三个大段的开头最为清楚,先知在每一处都呼喊说שִׁמְעוּ(“听啊!”弥1:2,3:1,6:1)。在前两章的信息中,他的“听啊”是对世上的万民而发;他在第二大段的开头特别呼吁“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来“听”;在末段中,弥迦呼召各山岭坐在陪审席上“听”耶和华向被告以色列所发的控诉。
以赛亚书最后一大段(赛40-66章)是用一个“结语”紧密组织起来的,就是“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赛48:22,57:21;卷末的66:24是这概念的延伸)。因此,以赛亚书40至66章可分为三大教导部分,每部分包含九点(各点和我们目前所分的九章大致相同)。
以重复词汇来划分段落,用得最多的应该是阿摩司书。几乎每个人都会注意到,在阿摩司书1-2章中有八次重复这样的句子:“三番四次地犯罪”“因为他……”“我却要降火在……烧灭……”(摩1-2章)这个大段的范围就极其分明了。
在解经者想要区分较难判断、较含糊的大段之前,最好先仔细查看阿摩司书其他大段的特征,这些段落在文体上也有明显的特征。阿摩司书中间的大段,即第3至5章,每章的开头都用祈使语气的שִׁמְעוּ表示。每个大段都有自己独特的特征、主题和宗旨。
阿摩司书第3章用了九个反问句。这些反问句确定无疑地引向阿摩司讲论所针对的因果结论:“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摩3:8)。此外,阿摩司书第4章的灾殃交替更迭,共达五次之多,每一次描述完神的审判,总是重复一句悲哀的感叹:“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摩4:6、8、9、10、11)这一切渐渐带来高潮——神那恒久忍耐的仁慈要有个了断:“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见你的神”(摩4:12)。阿摩司书第5章也以“以色列家啊,要听……哀歌”开始,重复“寻求”和“存活”等词:“要寻求我,就必存活”(摩5:4);“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摩5:6);又有“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摩5:14)。
接着,阿摩司书进入一个过渡性的大段,包含几个控诉,大部分包含“有祸了”一词(摩5:18,6:1、4;摩5:21的表达“我厌恶……不喜悦……”也有同样的作用)。
最后,全书以五个异象作结,其中四个都是以“主耶和华指示我”开始(摩7:1、4、7,8:1;而摩9:1也有同样的表达)。这末段的两个部分似乎与它的完整性不和谐:一个是叙述(摩7:10-17),一个是从“听”的呼吁开始的讲论(摩8:4-14)。在这里,解经者的工作是辨别出作者为什么以这种特别的方式安排书中的材料,我们应该设法解释它紧临的语境的位置和顺序。若没有抓住问题的要领,通常会使我们错过作者的整体目的和计划。在谈到紧临的语境时,我们会更详细地讨论这个话题。
除了我们所列举的,读者还会碰到其他例子。当然,如果一个大段的主题在经文中有很明显的提示,那就再好不过了。比如哥林多前书12:1说“论到属灵的恩赐”,就是一例。事实上,几乎整本哥林多前书都用περὶ δὲ(“论到……”)的结构,开始保罗所要讲的下一个题目(如林前7:1、25,8:1,12:1,16:1)。显然,保罗针对哥林多人在信中问他的问题是以一系列答复的形式组织他的材料的。
然而,解经者还是必须留意一些例外的情形,这些例外甚至会穿插在一贯的形式之中。哥林多前书6:12和10:23(我们只举两个明显的例子,不牵涉到像林前14:34-35之类的难题)是保罗从哥林多人的来信中引用的句子(该引句显然反映了他们的见解),而没有沿用大段开头的惯例:“论到……”
但是,在类似以上的所有例子中,我们知道我们正在处理的是引用,而不是作者自己的观点,因为这些情况都具有一个或多个下列特点:(a)引语与紧临的语境形成强烈对比;(b)作者暗示读者对该主题的了解;(c)引语的陈述跟作者所写的其他段落形成显明的对比。由此可见,当保罗说“凡事我都可行”(林前6:12,10:23),紧接着又以“但不都有益处”对应时,他的前一句一定是引用哥林多人的看法。之后,又同样是针对哥林多人“凡事我都可行”之观点的答复:“但不都造就人”及“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它的辖制”。
至于有争议的哥林多前书14:34-35,会不会是引自拉比的律法?它显然不是引自旧约,因为旧约并没有一处说到“妇女……要闭口不言,因为不准她们说话。她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她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这里我们同样要注意,保罗其实曾经吩咐教会要教导女人,并且让她们学习(提前2:11);不但如此,他还指示说女人可以在教会中发言、祈祷,和男人一样(林前11:4-5;提前2:8-9)。难怪哥林多前书14:36的语境针对拉比的限制发出强烈的反驳:“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男人)出来吗?岂是单(用阳性的μόνους,而不是阴性的μόνας!)临到你们吗?”
不管你是否同意最后一个例子,只要根据哥林多前书的前两个例子,多半人会同意上述第三点。密切注意每一个可能有助于我们找出分段点的微妙之处,这可能与辨认明显的大段衔接点同样重要。
二、书卷的语境
至此,我们应该可以确认该卷书的整体目的和计划了,这些“零部件”合在一起应该能体现整本书。
在一些作品中,如传道书,作者明明地告诉我们他的写作目的:“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סוֹף]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הַכָּל全部〕”(传12:13)。同样,路加写他的福音书,为要叫提阿非罗“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路1:1-24)。另外,约翰一书的用意是复述那源自耶稣之福音的真实性,“使你们的喜乐充足”(约壹1:1-4)。甚至还有更明显的例子,约翰福音20:30-31说明,约翰福音所记载的神迹是经过刻意选择的,“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些都是卷书中的例子,明确说出卷书的目的,我们可以由此判断它们随着各个章节展开的总体进展。
不过,有些书卷的整体目的必须从它的内容来确定,或由大段与大段之间、段落与段落之间的衔接来确定,这对我们来说要困难得多。希伯来书就是这类书卷之一,由于它的写作目的没有明言,所以我们最好特别注意散布在各劝勉大段(Parenetical Sections)中的劝告短语(Hortatory Phrases),如“我们务要……”(参来4:1、11,6:1,10:35-36,12:1,13:15)。作者似乎特别谴责善变的心态,以及犹太社会不久前接纳的有关救赎观的混乱思想。从这个角度来判断,教义的大段强调新约救赎的法则超越旧约中显然是暂时的礼拜条例,逐渐揭示了有意义的书卷形式和写作目的的规律。
最难判断的是那些主要部分(甚至全部)是叙述体裁的书卷。我们在后面会更详细地谈到这个题目,但现在重要的是要注意,解释者的判断必须根据作者选用了哪些细节以及如何安排这些细节来做出决定。
以路得记这个简短书卷的叙述为例。可以肯定,作者在路得记中的关切点是出现在书的结尾部分的大卫家谱;但即使是这个细节也很难说明需要说的全部,尤其是今日我们要成功地讲解路得记的信息时。
罗纳德·哈尔斯(Ronald M. Hals)指出,路得记的作者在85节经文中引入神的名字有25次之多。[4]其中有9次用在为本书卷一个主要人物的祈福祷告里,重要的是,每个主要人物至少有一次成为这种祷告的对象。更令人惊讶的是,作者在不打断叙事的情况下,通过暗示显明其中每一个祷告都蒙了垂听。
作者的风格以不张扬和沉默为主,他没有把发生过(或没有发生)的事加上道德的解释或评论,这使得结论更富戏剧性,更有力量。原来这个家庭日常生活的大小事件,都在神善意的照顾之下,也都包括在救恩的历史中。“神计划的线”直接绣在“日常生活的锦帷上”,[5]连我们生活中最小的细节都在神的带领之下,这就是路得记反复出现的主题。
总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就作者的写作范围和计划而言,有四种方法可以确定作者的意向。
(1)先观察作者自己是否在序言、结论或正文中清楚地指出他的目的。
(2)硏究劝勉性章节(劝告语气),尤其是新约书信,借此可以得知作者对经文的真理和教导部分有什么应用。作者的劝诫常常会从他写作这卷书的特殊目的中流露出来。
(3)探究作者收集和编辑历史故事整体目的的线索之一,就是观察他“选取”哪些细节,以及如何安排这些细节的。
(4)若没有其他可用的线索,解释者就必须自行推断作者的目的。解释者首先要研究每个段落主题句之间是如何配合来解释某一章节的主题的;然后进一步研究所有章节的主题,并衡量章节之间和章节内部的联系。唯有完成了这一步,解释者才能有一点把握说出作者的隐含主题。
三、正典的语境
近年来教会对正典有了全新的强调,在这对正典的新强调中,有一个名字在最近所有的注释家中格外引人注目,那就是布雷瓦德·S.蔡尔兹(Brevard S. Childs)。[6]在他看来,正典分析必须专注于经文本身,也就是现今教会所用之经文的最后形式。虽然他也认定历史批判学(Historico Criticism)和传统批判学(Traditio Criticism)的方法有些道理,但撇开这些不谈,现有的经文形式仍有其完整性,必须有人按教会现有的圣经经文来讲解。依照蔡尔兹的看法,重组经文虽然重要,却完全属于另一个范畴。
因此,虽然他的作法并没有试图用正典分析排斥那些考虑外在引申教义(以鉴定经文)的工作,但是督促解释者在圣经经文的框架内工作,这个框架来自那些把它作为神圣经文定型和使用的人。这样的强调早就应该在这样一个领域出现,那就是使人忽略其他工作,单单把经文作为永生神教会的圣经正典进行研究。
蔡尔兹急于确定没有人将正典分析的方法与近代其他几种批判学方法相混淆,正典分析不是所谓的“新批判学”(New Criticism)、“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或“修辞批判学”(Rhetorical Criticism)。事实上,正典分析是寻求了解经文的“神学形态”[7],而不是寻求发现其原有的文学形式或美学的一致性。
蔡尔兹又解释说,他并不是在正典分析的名义下提倡格哈德·冯·拉德(Gerhard von Rad)“宣道解经”(Kerygmatic Exegesis)——或汉斯·瓦尔特·沃尔夫(Hans Walter Wolff)、克劳斯·韦斯特曼(Claus Westermann)、沃尔特·布鲁格曼(Walter Brueggemann)——的形式,他们都过于倾向使用形式批判(form-critical)的方法重组历史性的语境;他也不像传统批判(traditio-critical)的方法那样只衡量经文形成的历史。
蔡尔兹所坚持的是,不能脱离教会看待圣经,反之亦然。[8]圣经的每一段经文都必须被理解,不是将其本身作为“证明文本”;而是必须在其出现的那卷书的语境下,以及在整本正典的语境下理解。只有这样,圣经作为神之启示的见证者的规范效力才能被理解。[9]虽然蔡尔兹认可古近东历史学家从考证和批判的角度来处理这些书面材料,也同意可以区分出诸如J典和P典的不同来源,但他还是觉得只有现今在教会中存留下来的完整的、合并后的文本(这是由历代传统累积和编辑而成的),才能“继续在信仰群体中行使权柄”。[10]
现在我们要就此提出两点意见作为评价。虽然福音派人士只能赞扬蔡尔兹敢于将圣经按其自身的形式视为正典这一大胆的新方案。但遗憾的是,这样的正典一定会与作者基于当时历史的特殊性所表达的原意脱节。按照蔡尔兹的正典分析,一个新的历史关联是由正典的最后形式及其最后语境所决定的(这是他的看法)。当然,蔡尔兹承认正典有超越历史的能力,因而能成为神新鲜的话语面对每一代人,但他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最终,这一传统必需以某种形式被赋予权柄——只能留给教会来做这项工作了。这样看来,蔡尔兹最终会被带回罗马天主教鉴定正典——还有其他方法能够鉴定正典吗?相反地,我们要强有力地指出,作者自己和寻求正典的早期教会都坚称,经文的规范先于教会,也是教会的根基。
其次,我们要批评的是,不能把整本正典作为每一段经文解经的语境。我们主张“经文佐证”(Proof Texting,即使用单独的经文,而罔顾紧临或大段的语境)的使用当受谴责,并应当立刻停止。但在神学分析那一章里,我们会提到,教会(尤其自改教以来)总体上误用了“信仰类比”(Analogy of Faith)作为一种解经手段,从出现在段落之前的文本中提取意思或将意思引入文本,而该段落是最清楚地阐述教义的段落,甚至是首次阐述教义的段落。这样作不是“解出”经义,而是“解入”经义,是从时间上较晚期的经文中提取意思,强加到较早期的经文中,而唯一的理由仅仅因为它们都同样为圣经的一部分。
幸运的是,蔡尔兹也不赞成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及其学派的哲学释经法(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他们把圣经看成暗喻的储藏室,认为圣经对现今的世代仍有解释与主导的能力。[11]有意思的是,蔡尔兹的评断是:虽然利科处理经文的方式是“前瞻”(devant)的,而不是文本背后的内容,但他没有将圣经的隐喻放在历史上的以色列的背景中。相反,它们成了自由浮动的、脱离历史背景的隐喻。
蔡尔兹的评断很正确!但这也是我们对蔡尔兹教授的批评。他谨慎地要在由此产生的教会传统中肯定正典,却从宣称首先听到并且明白了启示的作者手中夺走了正典。我们如何看待他们所宣称的呢?当然,即使传统批判法(Traditio-Critical Methods)能够得到充分的证实(叫我们这多疑的人信服),这样的方法能够完全清除作者在经文中的每一个宣称吗?(当然,除非另一个人类正典被定为判断依据,也就是说,作者必须被撇弃。)我想这是不可能的,作者的一些宣称仍然存在。因此,我们虽然由衷地赞扬并欣赏蔡尔兹的新重点,也从中得到许多有益和有希望的踪影,但我们仍觉得其中有一个严重的缺失:正典夺走了作者在解经上的地位。
然而,正典的考虑势必要在一处被引入。在我们完成了释经工作,并确定了特定经文的作者真正要表达的内容之后,我们必须接着将它放入整本圣经的语境中,将神对该主题进一步的教导收集在一起,再拿来与所查的经文做比较。只要记住一点:正典语境只能是我们总结的一部分,而不是我们解经的一部分。
四、紧临的语境
还有一方面必须考虑,就是在一个大段中的“段落分析”(诗歌中称为“诗段分析”)。由于我们会另外用一章来讨论诗歌,在这里我们只谈散文段落。
研究段落的语境,可以像发现一卷书各大段间如何相互关联一样具有启发性。如果不知道所查考的段落与其所在大段之间的关联,解经者在解释该段落时就常会感到茫然。这就要再说一次,确定语境的首要工作是最重要的。
出埃及记6:14-25是一个好例子,说明解经者可以从理解和考虑紧临的语境中获得帮助。这段经文是一个看似乏味、了无生气的家谱,大多数基督教解经家以为这一段必然没有什么价值,因此常常跳过去,进到下一段。
然而,若是跳过这一段,解经者就会错失好几个既有意思、又有帮助的要点。首先,这一段是由基本相同的材料构成的,因此,它的前面一段(10-12节)和后面一段(28-30节)都提到类似这样的话:“要告诉埃及王法老……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我是拙口笨舌的人。”
其次,这个家谱中只列出雅各的三个儿子(流便、西缅和利未),并没有像通常那样列出十二个儿子来,这样作的目的是只需要叫摩西和亚伦出现在名单中就可以了。注意26节:“这是对那亚伦、摩西说的。”
为什么有必要提到流便和西缅呢?这家谱包含利未两个哥哥的理由何在?我认为是因为他们两位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都犯了严重的罪,也都领受了神的赦免之恩。摩西也是一样,他不是杀了人又逃走了吗?若是我们要问:“就我们所认识的摩西和亚伦,神为什么要拣选他们?”答案就是:“这是神向摩西、亚伦的祖宗所施的同样的恩典眷爱。”因此,当摩西想要逃避与法老进一步会面的时候,神温柔地提醒读者,摩西和亚伦只是管道,不要把他们与人类的呼召者和供应者相提并论。毕竟,他们不过是“那亚伦、摩西”——但他们还是蒙了神的呼召。
各段落之间和紧临的语境之间的关联性有下列几种。
(1)历史的:在时空中所发生的事实、事件之间可能有关联。
(2)神学的:一个教义可能取决于某些历史事实和环境。
(3)逻辑的:一个段落可能和整个大段中进展的观点或思路有关。
(4)心理的:在前段所陈述之理由的某些事物,可能会突然引发一个相关的概念,结果常常带进一个岔出的题外话或破格文体(Anacoluthon),也就是暂时离开所讨论和解释的内容,而谈到一个乍看来毫不相干的概念。[12]
加拉太书5:4说“你们……从恩典中坠落了”[13],这个例子说明,当经文有神学关联时,明白紧临的语境是多么的重要。如果这个陈述用它本身作自证经文,就会产生一个全新的神学体系。但是,如果拿保罗对加拉太人所说的话作语境,这个解释就大不相同了。保罗声称,如果有人辩称他是凭律法称义,他就必须准备持守全律法的每个细节,否则就会与基督隔绝。因为那些凭律法称义的人,是把自己隔离在恩典的范围以外。在这个语境中,“恩典”不能被理解为个人所体验到的神白白的、不配得的怜悯和生命;相反,“恩典”应该被理解为“基督救赎的福音体系”(gospel system of salvation in Christ)。
只有明白并重视紧临的语境,解经者才不致于走极端。作者有权按他的意愿定义他所用的字词,而语境就是解开部分词义的一把钥匙。
[1] Samuel Davidson, Sacred Hermeneutics Developed and Applied: Including a History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Earliest Fathers to the Reformation (Edinburgh . Clark, 1843) 240页。引自Milton S. Terry, Biblical Hermeneutics: A Treatise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New York: Phillips & Hunt, 1890;再版,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64) 220页。
[2]以上大部分观念和部分例子取自John Beekman和John Callow, Translating the Word of God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74) 279-281页。
[3]我们的分段情形和有关所罗门是否为作者的讨论,见Walter C. Kaiser, Jr., Ecclesiastes: Total Life, Everyman's Commentary (Chicago: Moody, 1979)。
[4] Ronald M. Hals, The Theology of the Book of Ruth, Facet Books: Biblical Series,编者John Reumann, 23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69),3-19页。
[5]同上,19页。
[6]见Brevard S. Childs, “The Old Testament as Scripture of the Church,” Concordia Theological Monthly 43 (1972): 709-722;同作者,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as Scripture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79) 69-83页;并Gerald T. Sheppard, “Canon Criticism: The Proposal of Brevard Childs and an Assessment for Evangelical Hermeneutics,” Studia Biblica et Theologica 4 (1974): 3-17。
[7] Childs, Introduction,74页。
[8] Brevard S. Childs, Biblical Theology in Crisis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70),103页。
[9]见Sheppard, “Canon Criticism,” 6页。
[10] Child, Introduction,76页。他所采用的文件理论,以及他所发现多层经文传统影响文章形成的现象,我都不尽同意。我所反对的主要不是在学理上,而是在方法上。见Walter C. Kaiser, Jr., “The Present State of Old Testament Studies,” Journal of the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18 (1975): 69-79。
[11]见Paul Ricoeur,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and Theological Hermeneutics: Ideology, Utopia, and Faith, Protocol Series of the Colloquies of the Center for Hermeneutical Studies in Hellenistic and Modern Culture, 17 (Berkeley, Calif.: Center for Hermeneutical Studies in Hellenistic and Modern Culture, 1976)。此文亦收录于Studies in Religion/Sciences Religieuses 5 (1975-76) : 14-33。
[12]此项分类见Terry, Biblical Hermeneutics,2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