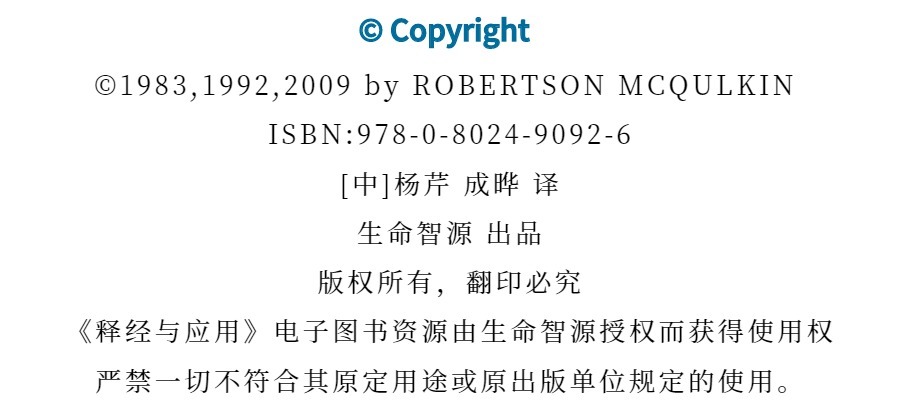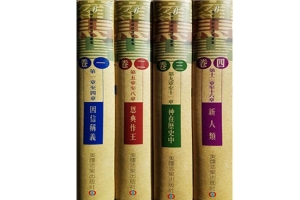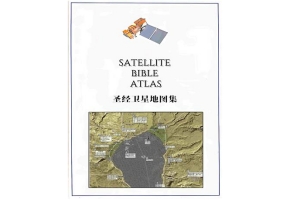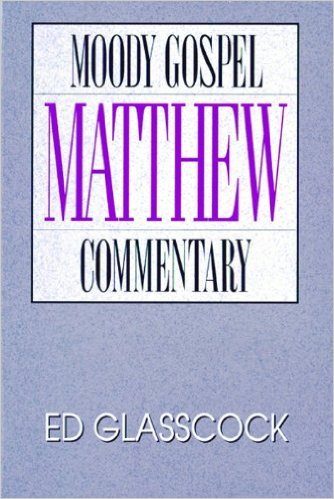关于圣经的权柄
唯有圣经是我们信仰和生活的绝对权柄。因此,所有诠释经文的原则和技巧都要顺应一个原则,即圣经本身是释经的终极权柄。下面我们查考一下这一原则的四个主要含义。
1.神启示的目的
神在圣经中启示自己的目的是为了人类的救恩。这救恩是完全的,从信徒最初与神和好,到生命得以更新而具有神的品性,到最后在永恒中与神在爱里联合。神的目的是人类的救恩。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后3:15—17)
既然说圣经的目的是人类的救恩,那就意味着神的启示是有限的。神给我们圣经的目的不是为了教导我们所有关于无限之神或宇宙万物的知识。神没有默示圣经作者提供一个古代历史的确切记录,也不是要教导我们所有关于人本性的知识。如果将圣经当成一本有关生物、心理或社会学的教科书,就等于错用了它,并且有损于它的权柄。毋庸置疑,当圣经涉及这些内容时,它是完全可信的,因为圣经不会教导错误的信息。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神教导的目的,相反,圣经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与神和好,并通过这种和好使人恢复神造人时的本来样式。
2.学习圣经的目的
因为圣经是关于属灵真理权柄的启示,具有独立权柄,所以我们研读圣经的初始目的便是要明白并确定作者的本意。
如果圣经的目的是为了我们的救恩,那么我们若不先理解圣经,这个目的就永远不可能实现。释经者的责任就在于此。但是,只理解圣经并不能带来救恩,我们还要相信并且顺服神借圣经传递的信息。这便是应用的责任。
解经若要忠实于作者的原意,必须包括应用。[1]
对神话语的学习只有通过被改变的生命才能得到印证……唯一可被称为“圣经教导”的教导,注重的不是处理信息,而是聆听和回应神爱的声音。[2]
总而言之,神启示的目的是为了人的救恩。人若要通过圣经得到救恩,第一步是要明白圣经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第二步就是凭着信心和顺服将这意思应用于现实生活。只有做到这两点,神启示的目的才能实现,圣经也才能在人们的生命中具有完全的权柄。
3.权柄的范围
我们已经看到,神的权柄并不取决于我们对圣经远不完美的解释,而只建立在圣经本身上。但是,这种权柄是仅仅存在于圣经的教导之中,还是延及圣经的字句呢?如果圣经所有的字句都具有权柄,那么圣经中的每一部分均具有同等的权柄吗?第一,我们的前设是,所有的经文都是神默示且完全正确的。此处我们无须重申圣经的默示性或无误性的立场,但我们有必要记得,我们释经的榜样是耶稣基督本人和新约作者。他们不仅把旧约看作是权柄性的,而且是完全值得信赖的,甚至经文所记录的单个文字也是如此。效仿他们的榜样,我们强调圣经的权柄时,不但指它表达的概念,也包括它所记录的文字。一些释经者承认圣经所传达的概念都是无误的真理,却认为圣经中有些文字是错误的。然而,如果所使用的文字不能忠实地表达意思,那所谓意思又从何谈起呢?更进一步来说,“所默示的概念”这一理论侵犯了圣经的独立权柄,使得圣经的权柄转移到了这些将正确的意思或概念与那些传递概念的不正确的文字区分开来的标准或标准的运用者。
蒙哥马利(John Warwick Montgomery)以法律文件作比来阐明这一点:
培根论述有关解释法律文件的通用原则时,说了这样两句名言:
“脱离法律条文字句的解释不是解释,而是占卜。”
“当法官偏离法律条文时,他就变成了立法者。”
伯罗斯(Roland Burrows)对此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法庭必须注意,证据决不能用来使当事人原来不完整的供词变为完整或与他所说的相悖,或以其他用字代替事实上的用字,或提出本不存在的疑问。对供词的解释一向只限于能帮助法庭理解所用字句的意思,以尊重所表达的本意。”
正如对待遗嘱、契约、法规一样,忠实于圣经的释经者会以确立其真实性的方式来解释经文,而不是否定其真实性。他们会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为前提,一旦确立了经文明确的意思,就会在生活中应用,“即使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会显得苛刻、不公平或者不便”。
那些真正的基督徒释经者也都认同,“一个遗嘱的每个部分都有它的意思,必须得到承认;如有可能,通过将它与其他部分相连、相协调来加以解释”。释经者会始终以“最后一份遗嘱为准”的原则,在新约的光照之下解释旧约。[3]
虽然所有的经文均出自神,并且是完全值得信赖的,但对于教会时代的基督徒来说,在顺服上并非所有经文具有相同的权柄。我们将在第十九章讨论应用圣经的原则时详细论述这一原则。圣经作为最终的权柄,必须自己指定哪部分经文具有持久、普世的意义,哪部分经文的含义是有限的。如果由其他原则或个人来区分普世和有限的含义,那么这个原则或个人就取代圣经而成了权柄。
4.权柄原则中的限制
圣经的权柄确实对圣经作者的背景以及经文的一致性这两个原则施加了具体的限制。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圣经本身就不是独立的最终权柄了。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限制。
对人的背景的限制。就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因为圣经是由人手写成,释经者就不可避免地要处理两个背景:(1)他力求尽可能完整地了解圣经作者的背景;(2)他力求根据当代背景解释并运用圣经的真理。通常,这两种努力是相结合的,也经常是相互交迭的。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在不侵犯圣经权威的前提下运用这些合理且有效的理解圣经的工具呢?我们在什么基础上区分圣经作者带有权柄的、永恒不变的教导和暂时的、历史性的背景呢?
人们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一些人认为,凡是那些与神的创造以及神的本性(如爱)一致的圣经教导都应该被相信并被遵守,但如果圣经的某一教导与创造以及神的本性无关,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断它是受制于短暂的文化形式或具体的历史背景的。他们认为,当代释经者必须重现这不变的真理,由当代人加以应用或拒绝。另一些人认为,凡是那些涉及普世性原则的命令,或在任何时代、文化背景下都被认同的道德要求(如不能偷窃),可以凭神明确的旨意的权柄应用于普世,但限于某一特殊文化背景之下的教导则不应该被如此应用。例如,圣经关于夫妻在婚姻中角色关系的命令是受文化限制的个别教导,因此不能以神明确旨意的权柄在所有的文化和时代加以应用。[4]
还有一些人认为,圣经中那些本身涉及道德与神学的教导具有权柄,而那些不涉及道德和神学的教导则不具有相同的权柄。[5]
所有这些观点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如何确定呢?既然圣经并没有给我们如此解释经文的基础,释经者或许不是有意为之,但还是因为用自己外在的标准来确定哪些圣经教导可以作为权柄被接纳,哪些可以被忽略,而篡夺了圣经的权柄。这个问题不是虚构的,解决的办法也不简单。但是,只有圣经本身才是对文化理解加以严格限制的不变原则。
到此,让我们来明确一下解释和应用的区别。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解释,也就是确定作者的本意。对于这一点,文化理解有助于我们明白经文的意思。其次,要在现实生活中应用经文,研究某一项具体教导背后的普遍原则是极为必要的。研经者通过这种方法可以确定并顺服神透过他满有权柄的话语所传达出的旨意。
下面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之前提到过的一个例子:
“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弗5:22)。
这话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显然,说这句话受文化局限不再适用于今天,这样的说法是行不通的。如果这样做,就意味着接下来这句“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弗 6:1),也应该作相对化处理,之前关于顺服神的命令也会遭遇同样命运。对于任何一位客观的释经者而言,保罗这句话的意思都是极其明确的。如果释经者承认神话语的独立权柄,那么他在解经的时候就不能改变这句话的意思,但关于如何应用这句话,则因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例如,美国家庭中的民主气氛可能会比日本家庭浓得多,但两个家庭可能都顺服圣经在这方面的教导。[6]
如果说为了将圣经应用在当代生活中的信心和顺服上,那么我们研究某一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圣经教导原则,就是合理且必要的。这样做不是侵犯圣经的权柄,而是在贯彻圣经的权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如果用这种办法来解释圣经,就会将经文明确的意思搁置一边,以当代的文化理解取代了具有权威性的经文。这样做不但侵犯了圣经的权柄,还成为一个操纵圣经教导的工具,使它迎合释经者想要的几乎任何形式。
寻求圣经所有教导合一性的限制。圣经的权柄限制了将圣经看作可以理解的人类沟通这一原则的实际运用,它也给释经者应当努力使圣经教导和谐一致这一原则施加了限制。在十五和十六章中,我们将学习寻求圣经教导和谐一致的具体指导原则和方法。
总而言之,在试图使一些看似互相矛盾的经文和谐一致的过程中,释经者主要在以下两方面侵犯了圣经的权柄:
1. 用那些晦涩的经文、不能确定的解释或圣经中次要的教导取代较为清晰、更主要的经文。表面上看,这只不过是经文之间的比较。但当一个不明确的教导被用来取代一个更明确的教导时,实际上是释经者或他对圣经的解释变成了权柄。
2. 释经者对明确的圣经教导进行逻辑性的演绎推理,从而侵犯了圣经的权柄。在以下这两种情况中,逻辑推理就侵犯了圣经的权柄:(1)当这种逻辑推理被当成完全无误的真理,甚至在其之上时。(2)当逻辑推理被用来推翻圣经中其他明确的教导时。在以上这两种情况中,逻辑推理演变成了圣经之外的哲学立场,被用来推翻圣经作者明确的原意。
如果神的话语要被理解、相信并顺服,圣经的权柄必须是至高无上的。
[1] William Larkin, Jr., Faculty Handbook (Columbia, S.C.:Columbia Bible College and Seminary, 1990), F-3.
[2] Larry Richards, “Church Teaching: Content Without Context,” ChristianityTo- day, 15 April 1977, 16.
[3] C.E.Odgers, The Construction of Deeds and Statutes(n.p.1956), 186, 188.John Warwick Montgomery, “Testamentary Help in Interpreting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Christianity Today, 5 May 1978, 55.
[4] Charles H. Kraft, “Interpreting in Cultural Context,” Journal of the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December 1978, 257.
[5] Gordon Fee, “The Genre of New Testament Literature and Biblical Hermeneu- tics,” in Interpreting the Word of God, ed. Samuel J. Schultz and Morris A. Inch (Chicago: Moody, 1976),133.
[6] See J. Robertson McQuilkin, “The Limits of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the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 June 1980, 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