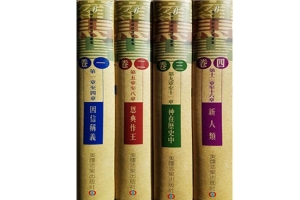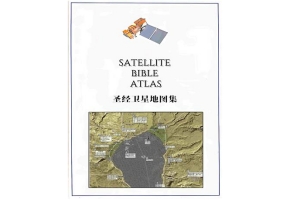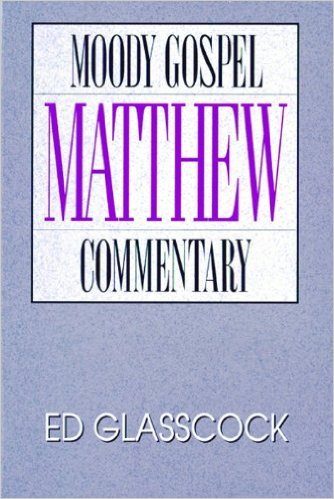“让我告诉你们两件事,如果你们知道了,可能就不会喜欢我了。第一,我是一个加尔文主义者。第二,我相信长老是合乎圣经的,应当由长老们带领教会。”
狄马可试图这样调动国会山浸信会聘牧委员会与他展开神学互动。1993年1月,有一位牧师结束了极短暂的任期,于是教会开始物色一位新的主任牧师。狄马可刚从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明白如果双方都要知道彼此是否合拍,这场对话就需要更有实质性。他们吃着中餐聊了好几个小时,还没有一个人对这位年轻候选人信什么提出任何重要问题。几年之后,我听狄马可把美南浸信会比作这样一个人:他开车的时候与另一辆车迎头相撞,这人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只记得一件事,那就是传福音。受伤之后,神学和教会论看来已经从这位美南浸信会之人的脑子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遴选的那个周末,狄马可讲了两次道,安排了一次全教会范围的问答时间,会见了教会的各个小组以及教会同工们。星期一早上,在上飞机之前,教会两位年长的成员与狄马可又开了一次会。这两位教会的教父级人物要谈什么?在他们周末听到的所有内容当中,只有一件事令他们不安:狄马可讲到关于长老的事情。
为什么这主题让这两人觉得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我怀疑有五个原因。首先,他们不熟悉这话题。他们做了一辈子浸信会信徒,对大多数20世纪的浸信会信徒提“长老”,这就像说天主教的“枢机团”(College of Cardinals)一样。这对他们是陌生的,甚至是隐秘的,因此值得怀疑。
第二,有一段缺失的历史。尼克松的电话录音磁带有一段著名的缺失,18.5分钟的内容没有了,但那与国会山浸信会的历史缺失相比就根本算不得什么。教会在过去几十年有大量圣经知识,大量可回忆的(地方)教会历史,但存在着1900年的空白,在此期间教会历史完全是看不见的。这就仿佛从使徒保罗到华理克这段时期,没有人曾经说过或写过关于教会的任何事情。
第三,这带有长老会的味道。逻辑是这样的:长老会有长老,我们不是长老会,所以我们没有长老。我们不确定我们为什么不是长老会,但知道我们不是。
第四,守旧。“不要改变任何事情,只要恢复原样。”教会曾经靠着这种不可能、做不到和不会错的智慧生存。讽刺的是,一位原本敬虔的女士,来国会山浸信会聚会几十年,但从来没有加入教会。她在教会同工当中传播着一篇题为《教会为什么不改变》的文章,这么做毫无帮助。教众已经非常擅长不作为。“勇敢”和“勇气”这样的词已经从他们的字典当中消失。
第五,他们害怕有人夺权。这其实是真正的罪魁祸首。虽然这些教父级人物说不清楚,但他们肯定,加设长老会涉及权力的重新分配,会把权柄给一些人,而他们对权柄不落在任何人手里感到非常满意。当时国会山浸信会有一层层的委员会。有执事委员会、女执事委员会、财务委员会、建筑委员会、房屋委员会、宣教委员会、讲道委员会、教牧委员会、鲜花委员会(没错,是鲜花)、以及众委员会之上的委员会。对教会里许多人来说,把权柄放在一小群人身上感觉会是个麻烦。
对狄马可来说,长老这观念既不是新的,也不是外来的。他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接触过有忠心长老的浸信会,甚至协助建立了一间这样的教会。在1991年所写的一封信中,他指导马萨诸塞州一间年轻教会的长老们在聘牧时要留意什么,并且列出了九点。关于教会带领,他写了以下这些文字:
第七,这或许是在你们开始时最困难的一点,我会要求这人能理解并坚信新约圣经中设立多位长老的做法(见徒14:23;保罗通常会提到任何一间地方教会的多位长老)。我完全相信这是新约圣经的做法,而且在当时和现在没有使徒的教会中也特别需要这样做。
这并不意味着牧师没有独特的作用(请查一查圣经经文汇编中提到讲道和传道人的地方),但他在根本上是众长老之一。这意味着,关乎教会的决定在还没有公布给全教会之前,不应当只是停留在牧师那里,而是应当带到全体长老面前。
虽然有时候这会很麻烦(我肯定你们非常清楚),但有极大的益处,能帮助牧师发挥他的恩赐,让他在教会中得到很好的支持,还有太多其他方面,我暂时无法都提到。
无论如何,聘牧的时候,应当把这一点讲得非常清楚。如果他是典型的美南浸信会背景,他会认为长老要么就是执事,要么就是协助牧师做他想要做的事。他很有可能没有意识到,你其实是在邀请他作众长老中的一位,就是在你们当中作牧师或主要的教导长老。
我深信,如果大多数牧师明白这一观念,他们听到的时候就会欢喜雀跃,因为这会卸下他们肩头的重担。我也担心有许多人不愿这样做,这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角色有不符合圣经的理解,或更糟的是,他们有未得成圣改变的的以自我为中心。[1]
为了纾缓群羊的恐惧,狄马可告诉他们,在没有长老的情况下他也乐意牧会四十年——他不想因为这个问题而分裂教会。但不管有没有长老,一些事情必须改变。考虑到会众的年龄、奉献的规律,以及城市的人口结构,维持现状是不可能的。然而,鉴于会众不愿改变,改变教会就不会是一件易事。
感恩的是,国会山浸信会确实聘请了狄马可担任牧师,1994年秋天,他开始在这群宝贵又多少有一些倔强的余民当中服侍。因为我的教会理事这个临时工作由90天不知怎么变成了好几年,那年秋天,他和我作为牧师与理事一起着手开始努力服侍。
现在,20年后回过头看国会山浸信会当时的改变,具体来说,就是采用众长老带领的改变,我可以很有信心地说四件事情:
第一,教会需要改变。我们一直在看着我们社区的许多老教堂被卖掉,所以我们对于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再清楚不过了——一些建筑物被拆,其他的被改造(恩典浸信会被改名为恩典公寓)。为了激发一些行动,我曾为我们教会的周报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我们的五年机会窗口》。而这个“窗口”正快速关闭。
第二,改变将会是孤独的。当时教会没有统一的异象,这种状态会一直持续,直到那些倔强的余民变成少数派。钟马田医生的女婿弗雷德·卡瑟伍德(Fred Catherwood)和狄马可在英格兰剑桥是同一间教会的成员,他在狄马可离开英格兰的时候对他说:“马可,请你记住,教会可能在五年后是你的,但一定不是在你刚到的时候。”对一位新牧师来说,一间老教会积累了许多人,这些人在不同的时期因着不同的原因而来,也受过不同人的牧养。狄马可的名字可能出现在告示板、信头和周报上,但他必须要很努力地去赢得他们的心,甚至要更努力才能把他们塑造成同心合意的一群人。没有多位长老在工作上的帮助,会让人感觉很孤独。
第三,改变将会是渐进的。为了改变一间缺少理解和信任的教会,大多情况下牧师会诉诸政治手段和操纵。毫无疑问,许多这样的牧师强行推动改变,超过了教会所能承受的。但我看到,狄马可却是缓慢而谨慎地前进。例如:
他在一周又一周常规的释经讲道过程当中谈论众长老这个话题。
他在带领聚会和牧养自己的家人时,都亲身示范长老在众人前和私底下该有的样式。
他慢慢让会众进入角色,在每周三晚上查经和每周日晚教会祷告会时向会众分发好书(20世纪90年代只有几本很好的关于长老这个话题的小册子,但它们都在会众当中传开了)。
当他的朋友卡森路过华盛顿特区时,他邀请卡森在主日学做一次关于众长老这个话题的演讲。
在这一切当中,他从未急于或强求改变。
几年后,是时候处理过时的教会章程了。教会又用了两年时间,由多人和多个小组重写了章程。一位邻居打趣说:“开国元勋写美国宪法都没用这么长时间!”当对这份纳入了众长老的新文件进行投票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反对——只有一个人!我认为这种反对票极少的情况表明了神的恩典,这是狄马可采取渐进、不急于求成的改变方式的结果。自从1947年以来就是国会山浸信会成员的卡尔森(Herb Carlson),在狄马可担任牧师十周年时发言说:“我不记得每一天发生了什么改变,但是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这是好节奏的标志。
这份新的章程读起来完全与狄马可所希望的一样吗?并非如此。狄马可和我写了初稿,指明了一个特定的方向,主要是把长老和执事的职分都包括在内。但经过其他人两年的编辑之后,这份文件写得更好,也与原稿偏离了几分,但没有任何根本性的改变。从中学到的教训就是:年轻的牧师常常太过于计较细枝末节,我们更应当关注大局。只要走在正确的方向上,我们就很高兴了。
第四,也是最后一点,改变是值得的。你宁可一个人牧养,还是希望在你纠结于教义、教会纪律和方向的问题时,有一群敬虔、合格的长老帮助你?萨拉离婚之后,按圣经能否再婚?是否应当把犯奸淫的阿本逐出教会?我们是要翻修培训侧厅,还是把更多的钱奉献给宣教事工?当一位牧师,就是要承担重担。你要肩负向神的百姓忠心传讲神话语的重担。你要承担犯罪之羊的重担。你要背负哀伤之人的重担。感谢神,在他的设计当中,一切重担是由多人承担,而不是由一人承担。如果有哪一位牧师身边有敬虔的长老们围绕他、支持他、托住他,你向他询问的话,他会告诉你,改变是值得的。
[1]这封信被略微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