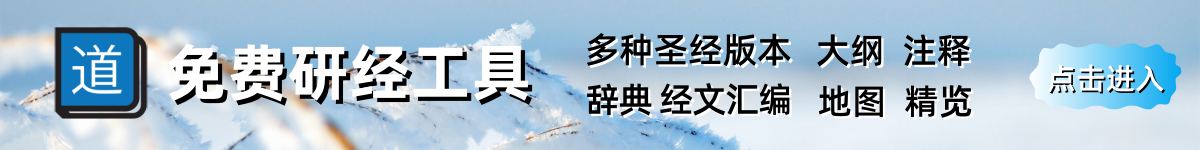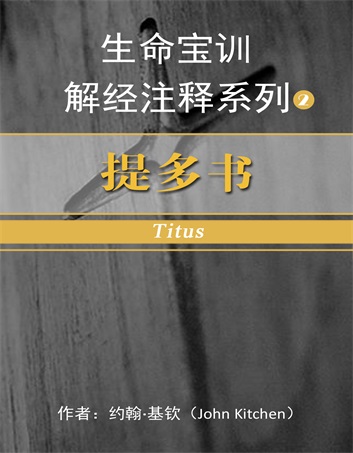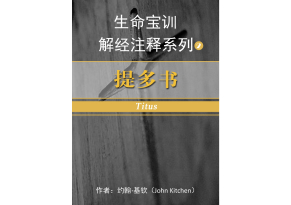导论
提多书是教牧书信中最短的一卷,因此常被篇幅较长的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夺去光彩。但这卷书在教义及实用价值上都极为丰富,值得加以研究。
一、作者
这卷书为保罗所写,这一点在初期教会无人置疑,其反对论调是近代才出现的。本注释毫无保留地接受本书为保罗所写。以下内容是本书作者对教牧书信作者所作的整体论述。
四福音书和使徒行传都未署名,我们在这些书卷上面对的问题是作者是谁,而非作者的真伪。但三卷教牧书信都以保罗之名起始,有关作者的争议便牵涉到一个关键问题,即这些书信的真实性。所以,我们必须颇为详尽地查考这个问题。
反对教牧书信为保罗所写的论据主要有四项,我们要对此一一加以答辩。
1. 历史方面的论据。教牧书信提到的事件与使徒行传的记载不符。使徒行传并没有提到保罗曾在克里特传道并把提多留在那里(多1:5),他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也与使徒行传的记载不符。关于这几点,所有学者都持赞同意见。
然而,保罗是否真的在使徒行传末尾几节所记的罗马囚禁时期被处死了呢?许多学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并据此认为这几封书信不可能为保罗所写。
我们的解释是:保罗第一次在罗马被囚后曾经获释,之后周游各处,在那期间撰写了提摩太前书与提多书。他写下提摩太后书却是在第二次监禁期间。
支持这种见解的证据相当可观。罗马的克莱门(Clement of Rome,“克莱门”又译“革利免”,公元95年)说,保罗曾到过“西方的尽头”(Clement 5)。对住在罗马的人而言,那个地方正是西班牙。保罗曾写信给罗马教会说,他计划路过他们那里前往西班牙(罗15:24、28)。《穆拉多利经目》(The Muratorian Canon,约公元200年)也提到了保罗“前往西班牙”。这证明他的计划最终得以实现。此外,我们只要留心阅读使徒行传就可看出,这件事只能发生在他第一次被囚罗马之后。
最明确的记载来自优西比乌(Eusebius)。他写道:
据称,保罗为自己辩护之后再次启程开展传道事工,后来第二次进入该城(罗马),并在那里殉道而死。入狱期间,他写下了提摩太后书,并于书中提到自己的第一次辩护以及即将殉道的事情。(《教会史》〔公元326年〕2:22)
2. 教会方面的论据。教牧书信中提到了监督、长老和执事。学者们宣称,这种教会结构要比保罗在世时的教会结构更复杂。
然而,我们若细读提多书1:5-9便可发现,“长老”和“监督”这两个名称是可以互换使用的。保罗也曾在腓立比书1:1问候腓立比教会的“诸位监督和诸位执事”。
《伊格纳修书信》(the Epistles of Ignatius,约公元115年)描述的情形则与此大不相同,那里说当时的每间地方教会都有一个监督、几个长老和几个执事。但显而易见的是,教牧书信反映的教会结构类型是保罗所熟悉的,而不是伊格纳修熟悉的。因此,今天许多人主张的教牧书信写于2世纪的观点,似乎并不符实。
3. 教义方面的论据。反对保罗是作者的第三个论据是,教牧书信强调的教义与保罗以前的书信有所不同,尤其是信中反复提到的“纯正的教义”(提后4:3;多1:9,2:1)这个短语。库梅尔(Kummel)虽然对此大作文章,却也承认“教牧书信极力反对的犹太基督徒之诺斯替异端……于保罗在世时就存在,这是可以想见的”[1]。他也说:“教牧书信出自保罗,这一点从2世纪末它们被承认为圣经正典,一直到19世纪初,都无人置疑。”[2]
其实,保罗在给歌罗西教会的信中就反对过诺斯替思想。19世纪评论家的错误在于,他们认定诺斯替思想在2世纪以前并不存在。如今人们已普遍承认,这种思想在基督教出现以前就已渗入犹太教。只是我们没有证据证明诺斯替思想在基督教出现以前已成体系,关于这一点,埃德温·山内(Edwin M. Yamauchi)已在他最新的学术著作《基督教之前的诺斯替主义》(Pre-Christian Gnosticism)中做出充分证明。
4. 语言学方面的论据。反对教牧书信真实性最有分量的论据是,它们在风格及词汇上与保罗之前的著作不同。这是今天那些持否定意见的评论家所强调的重点。
哈里森(Harrison)发现,教牧书信中有175个词在新约别处没有出现过,有130个词保罗从未使用,却是新约其他作者用过的。通过某种逐页字词对照(word-per-page method)的方法,他发现教牧书信所用的新词急剧增加,于是据此断定这些后期书信并非保罗所写。[3]
上述统计对20世纪的许多学者产生了巨大影响。对此,格思里(Guthrie)回应说:“根据保罗书信中有限资料做出的数据统计无法顾及主题内容、写作背景和收信人的差异,而这些差异都可能是新词出现的原因。”[4]剑桥大学的统计专家尤尔(Yule)宣称,若想做好一项切实有效的统计研究,必须有约一万字的范例作基础。[5]教牧书信的研究显然不具备这种条件。布鲁斯·梅茨格(Bruce M. Metzger)肯定地说,哈里森对统计方法的运用已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Expt, 70:91-94)。
近年来有几位学者一直主张路加是代笔者(秘书),是他为保罗撰写了教牧书信。莫尔(Moule)写道:“我认为三卷教牧书信都是路加所写,但他是在保罗在世时写的,其中只有一部分出自保罗口授。”[6]仔细研究圣经的人会发现,有相当数量的重要希腊词仅见于路加福音、使徒行传和教牧书信,却从未出现于新约别处。看起来代笔者有时被赋予了相当大的自由来撰写手稿,而我们又知道保罗在写信时确实惯于请人代笔(罗16:22)。
在其有关教牧书信的著作(ICC, 1924)中,沃尔特·洛克(Walter Lock)曾着重为这几卷书信的真实性辩护。他注意到,教牧书信与保罗给以弗所长老的临别赠言(徒20:17-38)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处。他说:“这些书信与其他保罗书信拥有相同的来自教会作者的证据支持。”他还宣称,这几卷书的教义背景在本质上仍是保罗的风格(p. 25)。此外,洛克和格思里也指出教牧书信含有路加的语言风格。[7]
或许更重要的是,牛津大学的凯利(J. N. D. Kelly)在《哈珀新约注释》(Harper’s New Testament Commentaries)1963年版的那一卷里,对上文提到的所有否定论据都给出了充分的回答。经过全盘的审慎评估,他得出结论为:各种证据“显而易见地……倾向于传统理论对保罗作者身份的肯定。”(p. 34)洛斯图德(W. J. Lowstuter)在《阿宾顿圣经注释》(Abingdon Bible Commentary)中写道:“总而言之,证据倾向于支持保罗为这些书信的作者。”(p. 1276)
二、收信人
这封书信是写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同信仰做我真儿子的”(1:4)。后面这句附加说明显示出,保罗与提多之间的关系十分亲密。提多书2:6-7则表明,保罗给提多写信时,提多还比较年轻。
圣经论及提多的话格外地少。虽然提多与保罗关系密切,但他的名字从未在使徒行传出现。除了这卷提多书,他的名字只见于另外三卷保罗书信(林后2:13,7:6、13、14,8:6、16、23,12:18;加2:1、3;提后4:10)。
按年代次序来看,圣经第—次提到提多是在加拉太书2:1-3。那处经文记载,保罗从安提阿前往耶路撒冷与教会领袖们讨论“他的”福音时,带着一个未受割礼的希腊青年提多同去,为的是把他当作自己在外邦人中间侍奉成果的杰出范例。“做我真儿子”—语暗示,提多是由保罗带领信主的,很可能就发生在使徒行传11:25-26记载的安提阿事工期间。他们在耶路撒冷期间,提多并未被勉强受割礼(加2:3-5),保罗认为外邦信徒不在摩西律法之下的立场也因此得到了肯定。保罗选择了提多来投石问路,试验一下这个关键问题,这充分说明这位青年归信者是满有属灵活力的。
在这之后,一直到保罗于第三次宣教旅程中抵达以弗所侍奉,圣经并未记载关于提多的情况。或许保罗当时曾带提多从安提阿同往以弗所(徒18:22-19:l),而在那里帮助他的那群人中就有提多,只是经文并未提到他的名字(徒19:22)。哥林多后书表明,提多这时已成为一位受人尊敬、且为保罗信任的同工。保罗曾不止一次打发提多到哥林多去执行重要使命。他很可能先后去过三次哥林多,但从哥林多后书来看,他探访该地的次数及时间顺序却无法确定。
大约在撰写哥林多后书的前一年,保罗曾打发提多到哥林多去,动员哥林多信徒为犹太圣徒奉献捐资(林前16:l-4;林后9:2,12:18)。显然,保罗在写完哥林多前书不久,便再次打发提多到哥林多去处理该教会的混乱之事,并挫败教会中的反保罗势力。保罗当时要去特罗亚宣教(林后2:12、13),便与提多约定事后在那里会合。然而,提多并没有按原计划返回特罗亚,这令保罗非常着急。于是,他放弃了特罗亚的事工机会,前往马其顿,希望可以早些与提多会晤。这时,提多终于在马其顿出现,并带来好消息:他在哥林多的艰巨使命已然完成(林后7:5-7)。此事的圆满成功令保罗十分喜乐,提多本人为哥林多人的回应心中欢喜,这也使保罗感到快慰(林后7:6、7、13-15)。由于事情进展顺利,保罗深受鼓舞,于是挥笔写下哥林多后书交与提多带回,并指示他办妥哥林多教会的捐资事工(林后8:6、7、16-22)。保罗极力举荐提多和与他同去的两个人(8:18-24),并向吹毛求疵的哥林多人保证,提多为人极其可靠,与保罗是同心合意的(林后12:17、18)。
后来,保罗在哥林多住了三个月(徒20:2)。那时,教会的问题已得到解决,捐资也已收妥。提多再次成功完成了一项棘手的任务。然而当保罗写下罗马书时,提多已经离开哥林多,因为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向罗马圣徒问安的那些保罗的同工中(罗16:21-23)。从此以后,一直到保罗撰写教牧书信之前,圣经均未提到提多。
保罗给提多写信时,他正在克里特岛上服侍。“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1:5)这句话显示,保罗曾与提多在克里特岛上同工。他们同工的时间显然不长,但足以使保罗认识到当地教会的不堪光景。保罗写下这封书信时,提多在岛上的侍奉显然已有时日。保罗通知提多,提多的接班人一到,他就要到尼哥波立与保罗会和(3:12)。尼哥波立显然是指希腊西部亚克兴海湾(the Gulf of Actium)伊庇鲁斯(Epirus)区的那个希腊城市。这个要求说明,保罗正为提多安排以后的计划。
提摩太后书4:10最后简单提到了提多。保罗在那里告诉提摩太,提多已往挞马太去了。这就暗示,保罗第二次在罗马坐监时,提多曾跟他在一起。虽然圣经没有明确交代提多去挞马太的原因,但我们可以推断,他必是带着基督徒使命前去的。
有关提多的这些只言片语表明,他是一位值得信赖、大有果效、颇受重用的年轻同工。他个性坚强、足智多谋、精力充沛、灵活老练,善于应对困难和解决纠纷。
三、写作情境
提多书外在的写作情境是,西纳和亚波罗计划路过克里特(3:13),他们会将这封书信带给提多。内在因素则是,保罗有心要巩固提多作为他的代表的地位,好让他在克里特完成一项艰巨任务。
四、写作目的
如上所述,这卷书信的写作目的之一,就是要鼓励并坚固提多完成保罗指派的使命。鉴于克里特的实际情况,保罗知道提多必会遭遇反对(1:10、11,2:15,3:10),因此需要巩固提多在克里特各教会服侍的权柄。这封信可谓是此项任务的授权书,它能向那地的会众证明,提多是按照保罗亲自指示行事的。保罗在信中表达了对克里特各教会的担心。作为保罗的亲密同工,提多想必对本书的劝勉和教导已经十分熟悉了。
克里特教会的起源不详。保罗到克里特访问时,那里的教会显然已存在一段时间了,但状况很是差强人意。他们在组织上十分松懈,所以提多受命要在各教会设立一些在道德和教义上都合乎资格的长老(1:6-9)。鉴于那里的假教师活动猖獗,这样做可谓至关重要(2:l-10,3:l-3)。基督徒的行为必须扎根于福音的基要真理(2:11-14,3:4-8)。
这卷书信也传达了保罗给提多的个人信息,信中指示提多在接班人抵达后,要赶紧到保罗冬天待的尼哥波立与他会合(3:12)。这其实是告知提多,保罗正在为他们的同工制定下一步计划。
五、写作时间
判断这卷书信的写作时间取决于两点:一是保罗第一次在罗马被囚的时间——人们普遍认为那个事件发生于公元61-63年,但也有可能在59-61年;二是保罗获释后的宣教之旅如何排序。由于这卷书信并未提及尼禄的逼迫(显然始于公元64年10月),因此将它的写作日期定在保罗获释与那次逼迫之间似乎最为合适。提摩太前书及提多书提及的那几次东行之旅,显然是在他获释后马上开始的。因此,提多书很可能写于公元63年秋,在保罗离开克里特后不久。
六、写作地点
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能推测。本书3:12表明,保罗那时尚未抵达尼哥波立。人们所推测的写作地点,无论哪种都取决于保罗获释后开展行动的先后顺序。其中一种推断便是,本书的写作地点为哥林多。
七、神学价值
提多书涉及的内容与提摩太前书大致相同,不过相对更为简洁、也更少提及私事。本书大部分内容谈的都是教牧职责及社会关系,但其中至少有三处概述性经文可谓神学瑰宝(1:1-3,2:11-14,3:3-7)。在提摩太前书中,保罗强调纯正的教义;在提多书中则强调与之相称的基督徒行为,并且强调基督徒的行为必须依据基督的真理,并受基督真理的制约。与其他书信相比,保罗在这卷简短的书信中更有力地强调了福音真理与道德纯洁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这卷书中,福音的基本真理透过其使人得救并成圣的不朽荣耀彰显出来。就经验来说,圣灵使人重生的工作是基督徒行为的根基(3:3-7)。
八、文本
提多书的各种原文抄本虽然有抄本之间常见的文字出入,但这卷书信的原文并没有特别严重的问题。联合圣经公会希腊文圣经的编者们认为,在他们所厘定的经文中,只有四处文本问题需要加注。
九、摘要
按照惯例问候之后(1:1-4),保罗首先论及教会长老当有的资格(5-9节),然后谴责那些暗中破坏克里特事工的假教师(10-16节)。
在第2章,保罗指示提多如何应对那里的状况。他定下基督徒的行为准则,特别论及年长的男子(1-3节)、青年人(4-8节)和做奴仆的人(9、10节)。
该章最后几节(11-15节)一直到第3章探讨了基督徒生活的社会影响(1、2节),反映出其神学上的侧重点。接着,保罗提醒人们思想福音带来的更新,这福音是借着救主的显现和工作成就的(4-7节)。
之后是有关行善(8节;参见14节)和假教师的劝诫(9-11节)。这卷简短的书信最后以有关个人的信息、忠告以及祈福结束(12-15节)。
[1] Feine-Behm-Kummel,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Abingdon, 1966), p. 267.
[2] 同上。
[3] P. N. Harrison, The Problem of the Pastoral Epistl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1).
[4] Donald Guthrie, New Testament Introduction: The Pauline Epistles (Chicago: InterVarsity, 1961), p. 221.
[5] G.U. Yule, The Statistical Study of Literary Vocabulary (Cambridge, 1944).
[6] C.F.D. Moule, “The Problem of the Pastoral Epistles: A Reappraisal,” in Bulletin of John Rylands Library, vol. 47 (March, 1965), p. 434.
[7] Donald Guthrie, New Testament Introduction: The Pauline Epistles (Chicago: InterVarsity, 1961), p. 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