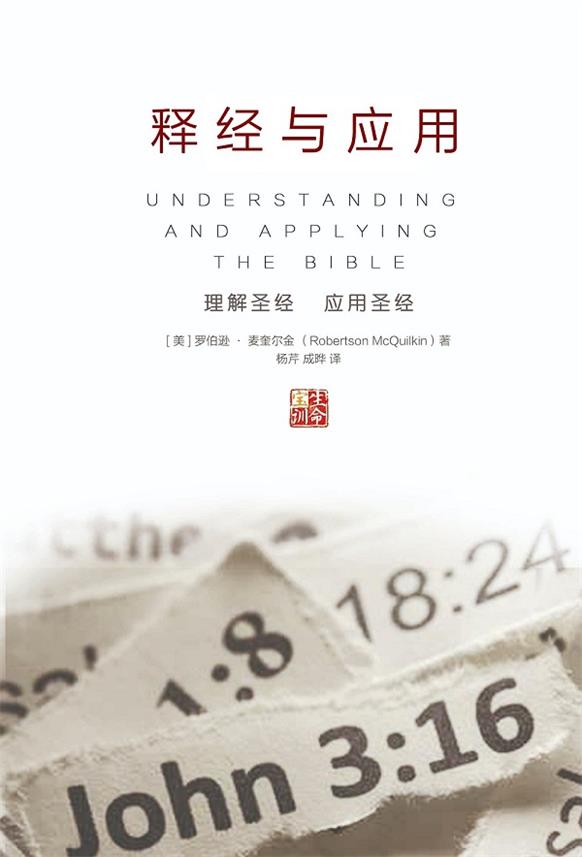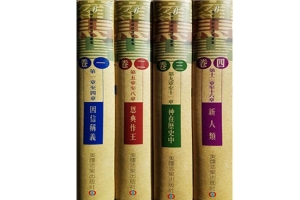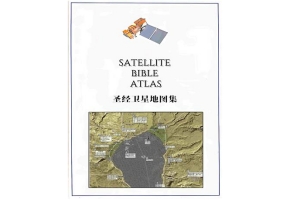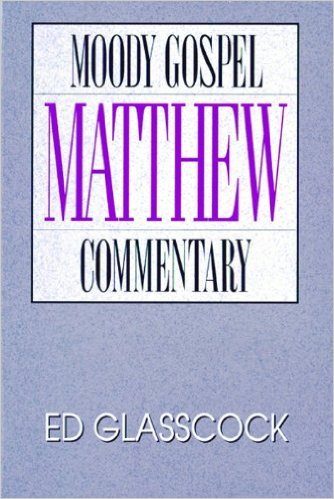第二章:前现代的超自然主义释经
我们已经看到,耶稣本人立下榜样,新约作者们继而效法,将圣经作为超自然的典籍处理。圣经中提到的某些器物(如铜蛇)、某些事件(如以色列人出埃及)、某些话语(如预言先知以赛亚得子)以及某些人物(如麦基洗德)都被视为对基督的预表。其中有些经文非常明确,足以让基督以前的犹太旧约释经家们一致看出它们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
然而,对于探寻圣经作者本意的人来说,则无法从许多经文中看出预表的含义,包括以上所举的例子。非信徒会说所谓的意思是被强加于经文的,信徒则会说经文的意思原本是隐藏的,要由基督或他的使徒将它们揭示出来。但无论如何,圣经都被视为是超自然的典籍,因为仅靠人类智慧,未来事件不可能在事发多年以前被准确且详细地预告。
犹太释经家和早期教父
对于犹太听众来说,耶稣理解及解释圣经的方法并不陌生。尽管有些犹太释经家将旧约当作一部应从文字的表面意思来理解的文献,但与耶稣同时代的大多数释经家都把探索旧约暗示和隐藏的含义作为己任。
犹太拉比释经(估计也包括早期法利赛人释经)的核心概念就是“米德拉西”(Midrash)。“米德拉西”指的是一个解经家通过穿越圣经的字面意思,以求深入到经文的属灵层面,从各种角度查考经文,从而挖掘出不能被人一眼看出的解释。[1]
犹太人的寓意解经(认为圣经真正的意思隐藏在文字的背后)与新约作者对待旧约的方式之间存在相似之处。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新约并不以这种方式对待所有旧约经文。不但如此,新约中也找不到那种极端且怪诞,属于典型犹太拉比式释经的结论。
后使徒教会时代的圣经学者们倾向于跟随犹太拉比,尤其是希腊的寓意释经者,而不是新约作者们。尽管当时安提阿的一群学者,包括克里索斯托(Chrysostom)、摩普绥提亚的西奥多(Mopsuestia of Theodore)和狄奥多勒(Theodoret),致力推断圣经作者从字面上传达的意思,但这一派学者的思想并没有在教会中占主导地位。
早期著名的北非沙漠教父克莱门(Clement)以及他的门徒亚历山大的奥利金(Origen of Alexandria),设定了宗教改革前几世纪教会释经学的基调。奥利金认为,利百加为亚伯拉罕的仆人和羊群打水的属灵含义是,信徒必须来到圣经这口井边才能与耶稣相见。克莱门教导说,基督喂饱众人的五个大麦饼代表希腊人和犹太人在麦收前所要领受的预备培训,二条鱼则代表了希腊化的哲学,指学习课程与哲学本身。在耶稣荣入圣城的故事中,驴子代表旧约,基督所骑的驴驹代表新约,而把驴驹牵到耶稣面前的两位门徒则是道德和属灵的象征。尽管克莱门相信一段经文有可能同时具有字面和属灵的双重意思,但奥利金坚持认为圣经中的所有记载都有修辞性的含义。
从4世纪到16世纪,这种被称为“四步解经法”(quadriga)的释经方法在教会中的地位坚不可摧。这种方法被用来分析每段经文的四种含义:字面性、道德性(借喻性)、神秘性(寓意性)和预言性(属灵性)。一段流行的顺口溜被用来教导这种解经法:
字词教导父神已成就之事,
寓意教导我们应信之事,
道德伦理教导我们日常应做之事,
预言教导我们应盼望之事。
“耶路撒冷”一词的含义就是个现成的例子。“耶路撒冷”的字面意思是以此为名的城;从寓意角度来看,它指教会;从道德伦理的角度看,它指人的灵魂;从属灵性的角度来看,它指天上的城。[2]
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花时间探究这一古代的解经传统呢?因为在21世纪初的今天,有一些圣经学者热衷于重新发掘早期教会先辈的智慧,再加上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他们正在倡导回归四步解经法。
改教者们强烈反对这种解经法。路德、加尔文和茨温利(Zwingli)关注探寻圣经作者的本意,以此作为信心和操练方面的权威。这三位改教者一致反对教会作为圣经的诠释者。他们都强调在理解圣经时个人所具有的自由、能力和责任,都认为神话语的权柄高于其他任何权柄。他们认为整本圣经都是可信的,所以经文能够也应该互为注解。另外,他们认同理解圣经需要圣灵的光照,但勤奋扎实的努力也是必需的。但具体在应当如何解释圣经上,他们并没有完全达成共识。
改教者的分歧在于,加尔文更为严谨一致地遵循上述原则,他严格按照经文的字面意思来解释。路德则没有那么精确,他时不时会寓意解经,以巩固自己的神学思想。路德的解经较为教条,受制于他所坚信的“得救本乎恩,出于信”的神学体系。另外,路德的解经有时具有很大的主观性,他甚至宣称自己得到了圣灵的直接光照。[3]
尽管改教者之间存在上述种种差异,但他们都齐心持守新约作者的前设:(1)圣经是人写成,但是由神默示;(2)圣经直接传达了神对人的旨意;(3)圣经的语言是普通人都能够理解的。
改教者们搭建了一座桥梁,使得释经从教会早期和中世纪令人难以捉摸的臆想过渡到了新教时期。这时,圣经作者的本意成为想要理解神的话语的人追寻的目标。但是,改教者虽然打破了寓意解经的桎梏,却导致了另一个后果——理性主义者此时得以自由阐发他们的观点。在宗教改革的同时,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主义观念在世俗世界兴起。很快,就有人开始把圣经看作一本普通的文学书。最终,自然主义解经方法成为新教解经的主流。
当代的寓意释经者
虽说改教者们把教会从那些视圣经为完全超自然、甚至具有魔力的人手中解放了出来,并且努力使教会回归圣经原貌,但人若因此认为寓意解经法就此绝迹,就犯了大错。
的确,这种解经法不仅仍然存在,而且兴盛,尤其是在福音派的圈子里。请思想以下这位拥有广大读者的著名解经家对圣经的解释:
“第三,在这种场合,神要求百姓静默,这条命令为该事件呈现的典型画面又增添了重要的一笔,尽管它对于今天的许多基督徒来说并不那么受用。以色列人攻陷耶利哥城明白无误地预表了神通过福音取得的胜利,吹公羊角的祭司所展现的是神的仆人传讲他的话语,而禁止百姓开口则表明普通信徒不可参与宣讲“真道”,他们既没有资格,也没有被呼召去宣讲神的话。
使徒书信中没有一处勉励平信徒去公开给人传福音,甚至也没有一处鼓励他们从事“个人事工”或去“赢得灵魂”。恰恰相反,他们要在工作岗位和家庭生活中以每日的行为来“为基督做见证”。平信徒要用好行为来“展现”对神的赞美,而不是用嘴巴宣讲对神的赞美。他们要在人前作光,他们用生命所做的见证远胜过无物的空谈。行为比言语更有力。”[4]
如果我们说经文虽然只有一种意思,但有不同的应用,以此来为这种释经方式开脱的话,是行不通的。诚然,一段经文有可能在当前的背景下有多种应用,但上述这种与作者本意相去甚远的释经方式,是典型的轻视作者及其原意的释经。在这种释经方法中,圣经失去了权柄,不能自由地表达它自己的意思,也不能要求人们顺服它的教导。相反,释经者通过寻找经文中的某个隐藏意思的寓意解经法,表达他自己的观点。
用这种方法释经,让人兴奋的“解释”所受的唯一限制,是研经者的独创能力。当直白的历史事实被传道人当作具有令人兴奋的属灵真理和隐含意思来传讲时,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福音派基督徒在灵修和寻求神的带领过程中都以同样方式利用圣经。很多在灵修中阅读圣经的基督徒,只有在从经文中找到某个令他感到意外的意思时才感到蒙福,而这意思与圣经作者的原意并没有直接关系。对他们来说,通过仔细研读圣经、明白作者本意来寻求神的旨意,似乎是枯燥乏味的。
同样,很多基督徒用读“魔法书”的方式来使用圣经,为自己必须做的决定指引一个具体方向,比如说,去哪里,买什么东西或接受哪份工作等。他所有这些决定都是从那些借着神奇的巧合并具有双重意义的经文中发现的。首先,这里有作者想传达的本意,同时还与他们自己目前的经历不相干的对应。比如,一对年轻夫妇可能正在为他们目前在美国某个山区的工作和他们想要去海外某个岛国做宣教士的心愿寻求神的带领。在读经时,他们发现了这样的指示:“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申2:3)。接着,夫妇俩又发现了另外一处预言:“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赛42:4)。虽然他们所领受到的与作者想要传达的信息毫不相干,但还有什么比这些具有权威性的经文更明确的指引呢?
我并不是说神从来没有通过此类巧合引导人。神可能这么做,正如他的引导也包括在生活中“偶遇”某人。然而神给我们圣经的目的并不在此,这种为自己的决定大肆宣称自己得到了圣经权威或神的支持,是滥用圣经。这种巧合完全可能在神的治理中发生,例如神借着当天的报纸引导那寻求神旨意的人。出于圣经作者本意的教导,人可称其为神旨意完全无误的启示,但对于上述巧合,则不能称为神旨意无误的启示。
如果用这种所谓来自于神的私人“信息”取代圣经明确的教导,例如某些禁止意欲之行的圣经原则,那便是更大的滥用。圣灵绝不会通过圣经作者们说一番话,然后为了读者说另一番话。换言之,神决不会通过任何偏离圣经文字的理解或应用来启示基督徒。如果神这样行,我们就不可能知道自己对圣经的理解是出于圣灵、我们本身的罪恶倾向、撒旦,还是出于某些心理或生理的刺激。
我们应当明确一点:若要圣经真正成为指导我们思想和行为的权威,那么我们对经文的主观理解就不能与其教导相悖。但是依赖个人对圣经主观印象的最大危害还不在于与圣经相悖,而在于超越圣经,找到绝非作者本意的含义。尤其是涉及个人的带领时,当自己的主观印象添加了神圣的权柄后,俨然成了神全然无误的话语。也就是说,将圣经当成指引个人日常生活的普通方式,容易让人产生错觉,认为它高于神在生活中其他治理之工的权柄,就因为这种“指引”是从圣经中发现的。
圣经应当用来教导人走正路,这正路由神对人类行为的旨意构成,这些旨意也必定与圣经作者的本意相符合。当某段经文恰巧与某人目前的境遇存在一定关系,且根据这种“启示”,这人做出了相应的决定,我们只能说这是个人在特殊情况下对圣灵带领的主观感受,而不应当称其为圣经的权威启示。
所有四种错误的释经法的本质问题,是主观主义。在主观主义中,释经者变成了圣经解释的最高权威。我们会发现自然主义释经法实际上也是主观主义的,因为释经者基于自己自然主义的前设,事先决定了圣经的哪些内容是可接受的。一种相对不太明显的主观主义,是灵意主观主义,那些深受其影响的人尤其不认为自己是主观主义的。
福音派容易犯这个错误,这可能是因为他们非常看重圣灵和圣经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要对圣经做出正确释解,圣灵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圣灵不但默示圣经作者,同时也启发数百年后阅读神话语的基督徒。默示意味着神指挥圣经的写作,甚至包括最微小的细节,而启发是指圣灵现今正在基督徒内心做工,帮助他们明白并正确应用神的话语。
根据圣经,神的默示意味着神的旨意全然无误,然而对于启发或圣灵帮助下对圣经的理解和应用,圣经则没有做这种保证。正如圣灵做工使信徒圣洁,而我们却尚未完美一样,圣灵也通过圣经启发我们,但这种启发的结果并不是我们能够准确无误地理解圣经。如果真能这样,那所有敬虔爱主的释经者对经文的理解就都会完全一致。当某个释经者把圣灵对他个人的启发看作是完全无误的,就如同他看待圣经一样,他就陷入了主观主义当中。在解释圣经意思时,某人宣称圣灵对他个人的特殊启发具有权威性已是不妥,然而他若将自己对圣灵带领这一主观感受等同于圣经本身的权威,那就错得更严重了,因为他偏离了神所默示的经文的本意。
这是否意味着正确的释经与主观的“蒙福”毫不相容吗?绝对不是!正确运用释经原则来理解和应用圣经、认识神的本意当然是神所喜悦的,这样做也一定会为个人带来祝福。圣经必须触动个人,否则就达不到更新我们生命的目的。然而,基督徒若想成长为基督的样式,不是借着改变神和他的话语来顺应我们的意思,而是借着改变我们去顺应神和他的话语。
难道只有一种意思?
每段经文只有一种意思,还是有隐藏之意,有待读者通过特殊的释经法则或圣灵直接的引导去发现?圣经中有这样一些例子,某个人得着启示之言,而这些言语的意思则启示给另一人。比如,在约瑟和但以理的经历中,言语和异象给了一个人,而它们的解释却给了另外一个人(创41;但2)。这种情况是否也发生在新约作者和耶稣身上?是否旧约作者有自己的本意,而神作为圣经真正的作者,则将另一层意思或更多的意思启示给一个新约的作者?
人们对于这个问题至少存在两种看法。一些人认为只要语言文字可靠,能够交流,一段经文就只能有一种意思。但他们并不否认一种意思可以有多种应用的可能性。此外,他们也不否认原本的启示可能包含更为丰富的含义。以关于神子受召出埃及的引言(太2:14-15)这个难题为例:很明显,这段经文所指的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何11:1)。既然如此,马太又是如何用这话指马利亚、约瑟和圣婴耶稣在埃及的寄居呢?这岂不是有双重意思吗?坚持圣经只有一种意思且这意思就是圣经作者本意的人认为,这段经文从一开始就是要表明神对主耶稣的计划。为了准备且预表耶稣基督将会从埃及出来,神允许他的子民以色列人在埃及寄居。事实上,神最早是将他的第一个选民亚伯拉罕召出寄居的埃及地。因此,在一开始经文就只有一个本意。但是,直等到那个“成全经上所记”之人来临,这段经文的完整意思才最终得以成就。
有些人却难以认同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对于某些经文不能解释为只有一个意思,这类经文的本意可能不止一个。这第二种(隐藏的或不甚明显的)意思可能是作者的本意,也可能只是默示作者的圣灵的本意。但不论是哪种情况,他们都认为这些额外的意思乃是出于神。圣灵将某一信息暗藏在经文中,之后将第二层意思通过另一个得到默示的人揭示出来(圣经中存在激烈争论的经文大都有关预言)。
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就是作者有权表达一个第二层或一个隐含的意思。若《一匹马拉车》(The One-Hoss Shay)的作者霍尔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的诗句不仅仅是关于最终散架的一匹马拉车,而是意在讽刺加尔文主义,这是他的权利。路易斯(C.S.Lewis)笔下的雄狮阿斯兰是不是基督的化身?问问作者本人就知道了!如果一位连环画家想将某个政治信息潜藏在自己的作品中,他也完全有权利这样做。事实上,这是一种常见的文学手法。但是有一条原则需要遵循,就是如果作者声明他没有别的意思,那么其他人就无权把某个所谓的隐含的意思强加给作者。换句话说,只有作者本人才有权认定他的作品中是否有第二层含义。
上述原则也同样适用于圣经,如果我们认为某段经文有第二层含义的话——是圣灵默示经文原作者,对作者所写经文的诠释也来自圣灵。
圣经作者的写作初衷是否同时包含一个直接的和一个更完整的意思?这个问题既复杂又相当重要。但是,我们的目的是建立理解圣经的前设,所以我建议暂且将这个问题放在一边。即便有人坚称每段经文只可能有一种意思,而且圣经作者对其最初意义和最终应用都了然于胸,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并非所有人都能真正洞悉经文更丰富的意思或它的最终应用。另一方面,如果有人认为圣经作者确实在某些经文中有意设置了双重意思,即一个是明显的,另一个则有待在将来被识别,同样,并不是任何人都能“破译”或者找到那个隐含的意思。
这一点非常重要。不管我们对于预言中隐含的第二层含义或者从一开始就预设的更丰富的意思持何立场,只有耶稣基督或那些受神默示的圣经作者,才是唯一能够识别那第二层的或更丰富意思的人。基督说话的时候,他本人完全有权对旧约作者加以解释,而那些经过基督授权,通过新约来揭示神旨意的使徒们也有资格这样做。
把隐含的意思强加给圣经的释经者,想当然地将自己等同于或凌驾于圣经作者。这样的释经者,不论是个人还是教会,实际上是在表明自己的权威甚至高过圣经。然而,唯有圣经才是神对他子民的旨意独立的、最终的权威。
神的启示在内容和领受的方式上的确是超自然的。圣经在那些读它、听从它的人的生命中具有超自然的功效,但这种超自然信息的载体却是人类的语言。如果经文真的存在隐含的意思,那也只有圣经作者或神才有权确定。基督徒若渴望明白并行出神的旨意,必须孜孜不倦地研读圣经,以便先正确地理解神的话语。他会致力于分辨圣经作者唯一想要表达的意思,而不是一味探寻隐含的意思。
若主耶稣本人或圣经作者已经点明在某段经文中的隐含之意,我们当然欢欣雀跃,而且也不会为此感到惊讶,因为圣经本来就是一本超自然的书,在所有作者背后都有一位创始成终的作者。然而我们必须把那一类解释留给圣经作者,因为神并没有任命我们来担当传递他额外启示的代言人。
推荐阅读书目
Blowers, Paul. M., ed. The Bible in Greek Christian Antiquity. NotreDame, Ind.: Univ. of Notre Dame Press, 1997.
Bray, G.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Past and Present. Downers Grove, Ill.:InterVarsity, 1996.
Fee, G. D., and D. K. Stuart. How to Read the Bible for All Its Worth. 2nd ed.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93.(戈登·费依、道格勒斯·史都华著,《读经的艺术》,中华福音神学院)
Dockery, David.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Then and Now. Grand Rapids: Baker, 1992.
Dockery, D. S., K. A. Mathews., and R. B. Sloan, eds. Foundations for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Nashville: Broadman & Holman, 1994.
Fairbairn, D. Grace and Christology in the Early Church.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2003.
Frei, Hans. The Eclipse of Biblical Narrative: A Study in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y Hermeneutics. New Haven: Yale Univ. Press, 1974.
Greenslade, S. L., ed.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ib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1963.
Hall, C. A. Reading Scripture with the Church Fathers. Downers Grove,Ill.: InterVarsity, 1998.
Hauser, Alan J., and Duane F., Watson, eds. A History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Vol. 1, The Ancient Period.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3.
Hays, John H., ed. Dictionary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2 vols. Nashville:Abingdon, 1999.
Kugel, J. L., and R. A. Greer, eds. Early Biblical Interpretation.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86.
Lubac, Henri De. Medieval Exegesis.The Four Senses of Scripture. 2 vol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8-2000.
Longenecker, R. N. Biblical Exegesis in the Apostolic Period. 2nd. ed.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9.
McKim, Donald K., ed. Dictionary of Major Biblical Interpreters .Downers Grove, Ill.: InterVarsity, 2007.
Muller, Richard A., and John L. Thompson, eds.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in the Era of the Reformation.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6.
Radner, Ephraim. The End of the Church.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8.
Saebø, Magne. Hebrew Bible/Old Testament: The History of Its Interpretation. Vol 1.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Middle Ages: Pt. 1 Antiquity.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6.
Saebø, Magne. Hebrew Bible/Old Testament. Vol. 1: Pt. 2. The Middle Ages.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0.
McNally, R. E. The Bible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Atlanta: Scholars Press, 1986.
Muller, R. A., and J. L. Thompson, eds.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in the Era of the Reformation.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6.
Oden, T. C., ed. Ancient Christian Commentary on Scripture. Downers Grove, Ill.: InterVarsity, 1998).
Smalley, Beryl. The Study of the Bible in the Middle Ages. Oxford: B. Blackwell, 1983.
Steinmetz, David C.“The Superiority of Pre-Critical Exegesis,” Theology Today, 37 (1980): 27-38.
Steinmetz, David C. The Bibl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Durham, N. C.:Duke Univ. Press, 1990.
Torrance, Thomas F. Divine Meaning. Edinburgh: T. & T. Clark, 1995.
Yardin, William. History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Peabody, Mass: Hendrickson, 2004.
Walsh, Katherine, and Diana Wood, eds. The Bible in the Medieval Worl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5.
Wood, James 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London: Duckworth,1958.
[1] S. Horovitz, “Midrash,” Jewish Encyclopedia, 12 vols. (New York: Ktav, 1904), 8:548.
[2] See James D. Woo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Duckworth, 1958), 72.
[3] 同上,87页及之下。另见Bernard Ramm, Protestant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Grand Rapids: Baker, 1970), 54
[4] Arthur W. Pink, Gleanings in Joshua (Chicago: Moody, 1978), 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