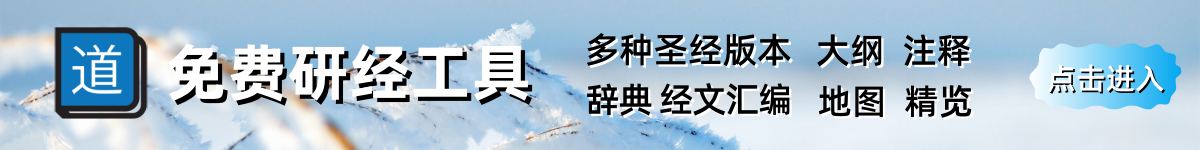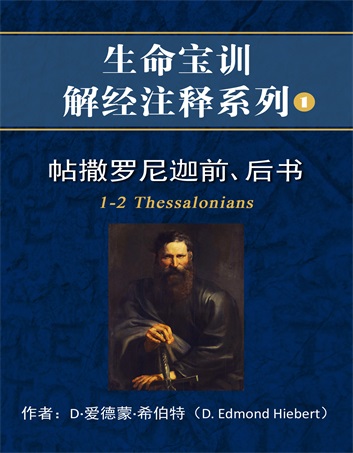帖撒罗尼迦前书导论
帖撒罗尼迦前书被贴切地称为一部“基督徒友情的经典著作”[1],因它是一封出之于作者和收信人之间温暖的属灵联结而写出的真诚书信。如果要准确地解读它,就必须对此信的历史背景有一个了解。跟研究其他文学形式相比,在研读一封书信时,对当时写作的生活环境有所了解更为重要。
帖撒罗尼迦城
地理位置
帖撒罗尼迦城的地理位置有着战略性优势。著名的伊格那修大道从它的城墙内经过,由东至西横贯整个马其顿。这条重要的罗马大道促进了旅游和商业,并将帖撒罗尼迦与其两边的重要内陆地区便利地连接起来。它是罗马与其东部省份交通往来的主干道。
帖撒罗尼迦坐落于塞尔迈湾(Thermaic Gulf)东北角的一个斜坡上,它还享有极佳的港口优势,其繁忙的海滨构成马其顿一带主要的出海口。它所处的位置能与地中海世界的其他各处有便利的海上往来。它在爱琴海区域的商业对手只有南边的哥林多和它东海岸的以弗所。在帖撒罗尼迦还算是隐蔽的港口中,可见到来自罗马帝国各地的船只。
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帖撒罗尼迦可以说是“马其顿全境的关键城市”[2]。梅勒提乌斯(Meletius)更是断言道:“只要自然条件不改变,帖撒罗尼迦将会永远富饶兴旺。”[3]当地一位诗人自豪地称之为“全马其顿之母”。
当地居民
帖撒罗尼迦这个繁华的大都市是马其顿最大的城市。哈里森(Harrison)估算其人口在保罗的年代可能高达二十万人。[4]
帖撒罗尼迦大部分居民是希腊本地人,但也有相当数量来自不同背景的罗马人、亚细亚人、东方人掺杂其中,还包括一群为数不小的犹太人。这个犹太族群经营了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会堂,使犹太信仰及其敬拜的形式在会堂里得以延续发展,并且影响了城中一群数量可观的外邦人归信犹太教。
一如所有的大城市,帖撒罗尼迦的市民也是贫富不一。富有的罗马人经常定居该市,市里成功的商人能够积累大笔的钱财。而大部分的居民则每日辛勤地靠经商或是苦力活来维持生计。
帖撒罗尼迦的居民大多为偶像崇拜者,所以此城的道德水准自然不会高过任何一般的希腊城市。它虽然没有像哥林多那样败坏的名声,但不道德的行为在那样一个偶像崇拜的社会当中仍是极为普遍的。这些捆绑当地居民的异教对社会产生了伤风败俗的影响。借宗教的名庇护,撒摩特喇众神卡比里(Cabiri)放纵的敬拜仪式使不道德的事滋生起来。[5]
帖撒罗尼迦的历史
公元前315年左右,马其顿的腓力王(Philip of Macedon)的女婿卡山德(Cassander)将该地一些村落的居民集合起来,并将他们迁到他新建的城市,就是帖撒罗尼迦。城市的命名是为了纪念他的妻子,她是亚历山大大帝同父异母的妹妹。
在公元前168年的彼得那战役(Battle of Pydna)之后,罗马人将所征服的土地划分为四个区,帖撒罗尼迦就成为第二区的首府。公元前146年,马其顿被罗马帝国规划为一个省份,帖撒罗尼迦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其首府。公元前42年,因为帖撒罗尼迦在与布鲁图(Brutus)和卡西乌斯(Cassius)的对抗中所做出的贡献,安东尼(Anthony)和后来成为奥古斯都(Augustus)的屋大维(Ocavian)将它立为“自由城”作为奖赏。
罗马的方伯,也就是马其顿的地方总督,当时住在帖撒罗尼迦,然而他并不管辖城市的内务,因为此城是“自由城”。和腓立比不同,此城没有罗马部队驻扎,其精神与氛围更有希腊风格,而不像一般的罗马城市。这个享有区域性自主权的城市由一群地方官来治理,其成员的数量有明显的变动。根据莫尔顿(Moulton)和米利根(Milligan)所说:“在奥古斯都的时代有五个地方官,在安东尼(Antonius)和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的时代则有六个。”莱特富特(Lightfoot)则说不是六个而是七个。[6]他们的头衔很独特,任何古典作品中都找不到“地方官”(politarchai,徒17:6)这个头衔。这一点曾被用来攻击路加之记载的可靠性,但已有石刻证据成功地印证了路加之记载的准确性。在帖撒罗尼迦本地出土的五六个石刻就都记载有这样的头衔,另有马其顿其他城市出土的一些石刻也证明这个头衔不仅限于帖撒罗尼迦城,它还出现在埃及的一些蒲草纸文稿当中。[7]帖撒罗尼迦城中显然还有一个元老院和一个公民大会。
这么多世纪以来,帖撒罗尼迦在兴衰变动中存留下来。现在的帖撒罗尼迦是希腊的一座重要城市,其人口超过四十万。新约里的重要城市能一直存留至今的为数不多,帖撒罗尼迦就是其中之一。
在帖撒罗尼迦的宣教士
保罗在特罗亚得到去马其顿传福音的指示(徒16:8-10),而福音在帖撒罗尼迦的传讲就是这个指示的具体实施。在保罗第二次宣教之旅的故事记载当中,路加在使徒行传17:1-10中对帖撒罗尼迦的宣教事工做了一个简要的叙述。
抵达帖撒罗尼迦
保罗和西拉在腓立比的事工卓有成效,但它触犯了帖城的既得经济利益,使他们遭受监禁和棍打,事工也因此戛然而止(徒16;帖前2:2)。路加这样记载宣教士们从腓立比到帖撒罗尼迦的行程:“保罗和西拉经过暗妃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徒17:1)。这是沿着伊格那修大道的行程,大约有一百英里。圣经中没有提到他们在沿途的两座城市中讲过道,这显然是因为这些城市中没有犹太人的会堂。并且,保罗似乎意识到帖撒罗尼迦的重要战略意义,它是向整个马其顿地区传福音的关键,所以保罗亟欲到那里开始讲道。
虽然保罗略过了这些城市,但这不代表福音不会在这些地方传开。恰恰相反,如罗兰·艾伦(Roland Allen)所指,竭力在一个省的一些重点城市内植堂是保罗的宣教策略,因为他确信福音会从这些城市传播到周边地区。[8]因此,帖撒罗尼迦在这个策略的实施中具有关键性地位。
我们并不能确定到帖撒罗尼迦的宣教团队具体有哪些人。路加所说的“他们”究竟都包括谁?(译注:“他们”是新国际译本〔NIV〕中徒17:1的主语。)路加之前使用“我们”表明他跟他们一起从特罗亚到腓立比(徒16:10,17:15),而这里突然改用“他们”,说明他留在了腓立比。提摩太是否也在腓立比逗留了一些时间呢?使徒行传没有提到提摩太在帖撒罗尼迦,而他再次被提及时是与保罗一起在庇哩亚。这是否意味着提摩太没有与保罗和西拉同去帖撒罗尼迦,而是在庇哩亚才重新归队的呢?扎恩(Zahn)认为,提摩太自然会在去庇哩亚的路上驻脚帖撒罗尼迦,借机探访新信徒。[9]伦斯基(Lenski)认为,这解释了提摩太为什么可以从雅典被差派回帖撒罗尼迦,而保罗和西拉却不能回去:他们“被赶出帖撒罗尼迦,而提摩太没有。提摩太遇到的困难较少”。[10]
因为提摩太的名字出现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问候语当中,一些人便认为提摩太一定也参与了那里的教会建立。从腓立比到帖撒罗尼迦的行程约百里,人们通常认为,提摩太是当时疲倦地走完这段旅途的那群人中的一位。解经学者指出,路加的关注点是记录福音的传播,而这不需要他指名道姓地记下团队中的每一个人。
只因为提摩太的名字出现在问候语中,并不能证明他参与了帖撒罗尼迦的初期事工,但可以证明他也跟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有紧密的联系。他若没有参与初期的福音传讲,就很可能是在去庇哩亚与保罗会合的路上和那里的信徒建立了关系。不过,帖撒罗尼迦前书3:5-6表明提摩太刚刚从那里完成任务回来,这经历也将他与那里经受患难的圣徒紧密地联系起来。
会堂事工
路加一开始就写到“在那里(帖撒罗尼迦)有犹太人的会堂”(徒17:1)。他这样描述保罗在会堂的侍奉:“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附从保罗和西拉,并有许多虔敬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17:2-4)。
路加说“照他素常的规矩”是要强调,保罗在一个新地方开展工作的常规做法,就是尽可能先在犹太人的会堂讲道。这不仅符合他“先是犹太人”的原则(罗1:16),会堂也是开始侍奉的最有利场所,因为那里有“为他预备好的听众,他们懂得他所传信仰的根本原则,也熟悉那些被他作为论述基础的经文”。[11]
保罗在会堂所讲的信息有两个中心点。他用旧约经文来向他的听众阐明关乎所应许的弥赛亚的重大事实。这些经文证明了这位弥赛亚“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对他们所期盼的弥赛亚必须受苦和受死的强调,对保罗的听众来说是闻所未闻的。传统的会堂教导并没有把弥赛亚与受苦联系起来,而是宣称他将会以以色列的护卫者和拯救者的身份来临。基于犹太法典的教导,布鲁斯(Bruce)总结道,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基督来临之前人们将旧约中关于他受苦的记载跟弥赛亚本身联系起来。[12]
通过巧妙地解释和比较经文,保罗确立了关于弥赛亚的这个重要教导。接下来,保罗向会众讲述了耶稣是怎样受苦、受死并且复活的故事,这故事正是经文中那些预言的应验,因此证明了耶稣“就是基督”。他是基督的事实当然也意味着他会应验弥赛亚将要掌权的预言,这也就自然带出了基督会以所期盼之君王的身份再来的教导。
保罗会堂里的听众包括两类:犹太人和“虔敬的希腊人”。其中第二类人通常更愿意接受保罗的信息。他们当中也可能包括一些“真诚寻求真理的异教徒”,[13]但这个术语通常所指的是一些外邦人,因为对异教的神祇和道德观彻底失望,转向犹太人更纯正的道德观教导。这些人成为非正式的会堂成员,他们敬拜耶和华,却不遵守犹太教那些严格的礼仪要求。尽管他们接受旧约一神论的教导以及对将要来临的拯救者的盼望,但他们
对犹太教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礼仪规定并不满意,并且他们对神需要有一个充分的概念,而基督教的到来满足了他们这样的需求。与犹太教相比,基督教所提供的是一个更大的神的概念,一个更崇高的道德观,以耶稣卓越的个人榜样为核心,还有一个普世性的眼光,这在犹太教狭隘的排他主义背景下简直就是一缕解放的清风。[14]
这样的会堂事工的结果是,一小部分犹太人和为数众多的虔敬外邦人归信了主,其中还包括城中一些尊贵人士的妻子。
停留的时间
使徒行传只讲到一连三个安息日的会堂事工。紧随其后记载的便是犹太人聚众攻击保罗和西拉,使他们不得不突然离开帖撒罗尼迦。那么宣教团队是仅仅在那里停留了三个礼拜,还是更长的一段时间呢?
如果我们只有使徒行传的记载,最自然的结论就是:他们的事工仅限于那二十一天,范围也局限在会堂的圈子里,并未直接接触市内的异教徒群体。然而另一方面,帖撒罗尼迦前书似乎清楚地表明,很多帖撒罗尼迦人是从异教中归信的(9:14,2:14)。显而易见的是,使徒行传没有完整地记载这故事的原委。
扎恩、弗雷姆(Frame)、伦斯基等解经学者认为,在帖撒罗尼迦的事工不可能比路加所提到的三个礼拜长很多。扎恩指出,会堂在周一、周四也有聚会,并且“在其他时间也是开放的,用作一些非常规聚会的场所”。[15]这就意味着在帖撒罗尼迦的事工是一个短期、密集的活动。弗雷姆认为,“一旦人们承认那群人为数不多,并且有着密集的信仰生活”,就不难理解短短三周的事工所能收获的果效了。[16]主张这种短期事工观点的人指出,构成帖撒罗尼迦教会主体的那些外邦人在那之前就已经被装备好接受福音信息,以至于保罗满有能力的福音宣讲能在短时间内得到那样大的果效。他们更进一步地指出,和在雅典一样,保罗在此地无疑也在周中的时候抓住一切机会向会堂以外的外邦人传了福音,[17]因此他很可能就这样从异教信仰群体中赢得了一部分信徒。另一方面,伦斯基坚决认为帖撒罗尼迦前书1:9和2:14那里“可以指进犹太教的希腊人,并不一定是从异教信仰中归信的人”。[18]因此,这些学者认为这一切事迹都可以在三周的事工内完成。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有充分的证据认为,他们在帖撒罗尼迦的事工时间远超过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三周。拉克姆(Rackham)认为,路加“特别指明在会堂教导三个礼拜,似乎暗示着那三周结束后他们便转向外邦人了,就如在彼西底的安提阿所做的”。[19]当保罗不再能进帖撒罗尼迦会堂,他的事工很可能就直接转向城里的外邦人。在以弗所,保罗在会堂事工结束后又继续在那里对外邦人做了两年的事工(徒19:8-10)。这些在会堂里得救的敬虔外邦人,很自然地成了他们联系城里广大外邦人的桥梁。
比尔(Beare)认为,“使徒们在那里传福音之后所做的教牧关怀(见帖前2:9-12),以及他们与那里的信徒所产生的深厚情谊(2:8,3:6-10),即使不能绝对地下结论,也至少表明,他们在那里停留的时间可能是几个月而不是几周”。[20]他还特别留意到帖撒罗尼迦教会显著的外邦特色,正如这两封书信中所反映的。他总结道,仅从帖撒罗尼迦前书来看,我们完全读不出“当时帖撒罗尼迦有一个犹太群体,更不用说这个群体还是宣教事工的中心并为使徒提供了教会的核心成员”。[21]比尔的说法虽然强调了帖撒罗尼迦教会外邦人的特性,但它忽略了保罗在2:14-16中针对犹太人所用的强烈措辞的真正原因。
主张延长逗留时间的人还指出保罗在帖撒罗尼迦靠手工劳动来供养自己(帖前2:9;帖后3:8)。格洛格(Gloag)认为,“他只有长时间居住在某个城市时才会这么做”。[22]这里的意思也许不过如此:保罗抵达帖撒罗尼迦时经费所剩无几,而他想要安排好定居一段时间。这种自给自足的做法对他的事工是必要的,因为它会杜绝人们的猜疑,即怀疑他的事工仅仅是一种赚钱的活动。
支持长期停留观点的一个更有力的证据是,当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做工时,腓立比的教会“一次两次地打发人供给我(保罗)的需用”(腓4:16)。虽然在三周之内多次接受供给不是没有可能,但其可能性不大。因为当时保罗自己从事工作,腓立比的弟兄不大可能会认为他有如此迫切的需要,而且他们也实在供应不起。保罗的用词“一次两次”(hapax kai dis,字面意思是“一次和两次”)自然的理解是两次,但弗雷姆试图将这节改译为“(当我)在帖撒罗尼迦,又有多次(当我在其他一些地方)”,从而削弱了这个论据。[23]虽然这种解读在原文也是有可能的,但另一种解释更为简洁。
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保罗和西拉到底在帖撒罗尼迦停留了多久。看起来更合理的观点是比三周长,并且那三周之后的时间是用来做城里外邦人的事工。具体停留了多长时间就只能靠猜测了。拉姆齐(Ramsay)认为,帖撒罗尼迦的事工可以长达六个月。[24]因为保罗觉得他过早地与信徒们分离,所以莫法特(Moffatt)提出的观点更加合理,他说“关于在帖撒罗尼迦的宣教事工时间,要有如此丰盛的成果可能需要两到三个月”。[25]
离 别
对于犹太人如何成功地迫使这些宣教士离开帖撒罗尼迦,路加生动地记载了他们的谋算:
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城的人闯进耶孙的家,要将保罗、西拉带到百姓那里。找不着他们,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耶孙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于是取了耶孙和其余之人的保状,就释放了他们。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西拉往庇哩亚去。(徒17:5-10上)
路加对在帖撒罗尼迦宣教事工的记载给人的印象是,在会堂事工的第三周后这场暴乱就紧接着发生了。但就算在犹太人暴乱之前还有一段对外邦人事工的时间,这个记载也一样说得通。那时,犹太人已经禁止保罗再去会堂,但他们仍满怀嫉妒地观察他在城里事工的进展。因为那事工已经超出了他们的管辖范围,如果不采取暴力手段将宣教士们驱逐出城,他们就只能在那儿愤怒而无可奈何地观看。
犹太人这么做的动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多年来他们都试图争取那些愿意接纳的外邦人,希望能他们能完全拥抱犹太教的信仰。但宣教士们的事工完全破灭了他们的盼望,因为使徒团队不仅已经赢取了为数众多的虔敬外邦人,同时使徒们在城里其他外邦人中所开展的如火如荼的事工更摧毁了犹太人赢得他们的一切希望。由于犹太人认为宣教士所传扬的是变质的犹太信仰,于是他们坚决果断地采取强硬措施来镇压这样的工作。
因为犹太人本身的力量不够抵挡宣教士,于是他们采取了一个卑劣的手段。犹太人从闹市的大量闲杂人等,就是那些游荡在闹市街区无所事事、寻求刺激的人中,招募了一些以惹是生非出名的市井匪类。借着这些人的帮助,他们集结了一群人,在城里兴起一波喧嚣的骚动。在聚集了足够多的人之后,他们攻击了耶孙的家,目的是要捉拿宣教士们。耶孙的家显然不仅为宣教士们提供了居所,也是基督徒聚会的场所。
这群由犹太人带领的暴民闯进耶孙的家,搜索保罗和西拉,要将他们带去见“百姓”,显然就是去帖撒罗尼迦的公会。他们因为找不到保罗和西拉,就把耶孙和其他一些基督徒拖到城市的统治者(即地方官)那里,指控他们为革命运动的团伙成员。他们被指控的罪名是收留革命分子,就是那些“搅乱天下的”。更确切地说,他们被指控有谋反的行为,因为他们“都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
这样的指控是精心设计的,并且明显体现出犹太人在背后的挑唆。保罗所教导的基督再来时要施行审判并作王掌权是很容易被曲解的,所以犹太人的指控当中包含一丝与事实相似的成分。保罗关于弥赛亚君王再来的属灵教导很容易被扭曲,说他倡导大家效忠于另一个王,这就是对凯撒的不忠。
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指控,地方官们对它一定非常敏感。这样的指控最有可能引起地方官对基督徒的敌意。然而尽管群众这样煽动,官员们却拒绝因为一时惊慌而采取暴力措施。反而,他们仅要求耶孙和同伴交付了“保状”,就放了他们。这也许是官员们识破了犹太人的计谋,看出这些动机是出于敌意,而不是对政府的忠诚。拉姆齐说,地方官这样的做法是“在对实际情况的审慎考虑下所能采取的最温和的措施”。[26]这样的做法既保证官员不会被指控为纵容谋反者,又不至于让基督徒受到不公正的伤害,还能让搅事者觉得他们已经对他们的敌人采取了行动。
至于他们从耶孙及其同伴那里收取的这个“保状”具体指什么,我们并不清楚。拉姆齐认为它是一种金钱保证或保释金,要求他们“要防止造成暴乱的根源(即保罗)进入帖撒罗尼迦”。[27]然而使徒行传并没有说他们要求耶孙保证保罗会离开帖撒罗尼迦。保罗自己说他曾两次试图返回帖撒罗尼迦(帖前2:17-18),似乎也反对这个推论。最有可能的解释就是,耶孙和弟兄们被要求交付保状,保证不会再扰乱城里的安宁。这样的要求实际上使保罗和西拉不能再在城里继续工作了。如果他们冒险继续在那里宣讲福音,犹太人无疑会再次引发骚乱,不仅耶孙和其他基督徒伙伴将面临重大的财产损失,而且也会引起官员们对教会的强烈敌意。
在这样的情形下,宣教团队同意了弟兄们的观点,认为权宜之计便是让保罗和西拉立即离开。他们这样被迫离别是因为无法控制当时险恶的环境,这也将保罗和那些新生的信徒过早地分开了。这年幼的教会失去了它所需要的宣教士的亲身引导,同时一波针对信徒的逼迫也由此而生。这样的逼迫在宣教士离去之后仍然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保罗书写帖撒罗尼迦后书时,对教会的逼迫仍在进行中,或者当时又重新爆发了(帖后1:4)。使徒行传和帖撒罗尼迦前书2:14-16的记载都指明逼迫的煽动者是犹太人,但很明显的是,由犹太人引发的敌意和逼迫也感染了他们的异教徒邻居(帖前2:14),使得他们也开始迫害基督徒。
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写作缘由及目的
写作缘由
保罗和西拉在夜幕的掩护下离开帖撒罗尼迦,向西行走了四十多英里来到庇哩亚。不论提摩太是否在帖撒罗尼迦与他们一起工作,他确实在那里加入了他们的团队。在庇哩亚会堂中开展得卓有成效的事工,再一次地被从帖撒罗尼迦来生事的犹太人搅扰。保罗是他们的敌意所针对的主要目标,爆发这样的冲突使他迅速悄悄地离开庇哩亚。
西拉和提摩太仍留在庇哩亚。一些庇哩亚的弟兄将保罗安全地带到了雅典。这些弟兄一回到庇哩亚,就向西拉和提摩太传达了保罗的紧急召唤,要他们急速去雅典(徒17:10-15)。
使徒行传记载,西拉和提摩太在保罗抵达哥林多后,确实在那儿与保罗汇合(18:1、5)。如果只有使徒行传的扼要记载,我们的结论会是:他们直到那时才得以遵从保罗的要求。但从帖撒罗尼迦前书3:1-5可以清楚地看到,至少提摩太,看来也有西拉,确实按要求去了雅典。
自从保罗被迫与在帖撒罗尼迦的归信者分开之后,他的牧者之心便深深地挂念着他们。保罗很清楚他们会承受自己所遭遇的患难。事实上,他之前就已经明确地警告他们,成为信徒就必遭受患难(帖前3:4),但当烈火一般的试炼实际临到身上时,他们能否经受得住呢?他自己亲身经历了帖撒罗尼迦犹太人强烈的仇恨,甚至到了庇哩亚仍是如此,这些只是加深了他对这些新近归信之人的担忧。既然那些犹太人可以一路纠缠他到庇哩亚,那他们对那些仍留在城里的跟从者又会做出什么呢?他完全可以想象他们将会经受到怎样的猛烈攻击。显然,提摩太和西拉带去的负面消息进一步加重了保罗的焦虑。
因为不清楚这一波迫害的风暴会对帖撒罗尼迦人产生怎样的影响,保罗的心产生了难以忍受的焦虑。既然不能再忍受这种忐忑不安的悬疑,他便决定打发提摩太返回帖撒罗尼迦,去鼓励那里的弟兄们,并且带回一些有关他们的消息。回帖撒罗尼迦对提摩太来说不是一件难事,因为在大众的眼里他与那里的动乱并无关联。很明显,那时西拉也被派遣去马其顿完成任务,也许是去腓立比。保罗很可能是担心帖撒罗尼迦犹太人苦毒的仇恨也许会波及在腓立比的信徒们。
撰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直接缘由就是:提摩太从那里回来,带来了关于他们的消息(帖前3:6-7,参徒18:5)。这消息整体来说是非常好的。它消除了保罗的焦虑,并且使他充满了赞美和欢喜。保罗以口授的方式撰写了这封信作为回应,信中充满了个人情感和谆谆教诲。除了此信,他只有在给腓立比教会的信中表达了同样的感恩,就是为他亲爱的读者所表现的坚定不移而献上的感恩。因为保罗不能亲自回去,这封充满了感恩和教牧性引导的暖心之信对帖撒罗尼迦人来说便成了最好的替代品。
但写这一封信,是不是为了回复帖撒罗尼迦教会托提摩太所带来的信呢?这个观点原为伦德尔·哈里斯(J. Rendel Harris)所提出,近期又有查尔姆·福(Chalmer E. Faw)提倡。[28]福主张说,这封信的前三章是回应提摩太带来的口头报告,而后两章则是逐条回应帖撒罗尼迦人在信中所提出的问题。他指出,4:9和5:1里面起引介作用的词语“论到”(peri de)也在哥林多前书中数次出现,在那里保罗是对哥林多人写给他的信做出直接的回复。但帖撒罗尼迦前书与哥林多前书并不完全相同。在哥林多前书中保罗明确指出他是在回复来信(7:1),但帖撒罗尼迦前书中没有任何线索表示他是在回信。哈里森恰当地指出,如果是因为保罗疏忽而未提及帖撒罗尼迦人的来信,这是相当不礼貌的。[29]福用作论据的这个词语,在新约其他一些地方的用法明显不是回复来信的(可12:26,13:32;约16:11)。福所表明前三章是回复口头报告,而后两章是回复来信,这些细节是难以区别的。
帖撒罗尼迦人有来信的假设本身是可以成立的,只是没有充分的证据来支持它。如果接受这个假设,就能构想出一系列可能回答的问题。但仅仅是能够重构出一系列假想的问题,并不能证明这封信真的存在。对腓立比书来说,类似的假想来信以及其中可能提出的问题也可以重构出来。这个假设缺少合理的依据。亨德里克森(Hendriksen)总结说:“一份由提摩太仔细准备的书面报告,或一份条理清晰的口头报告,便足以解释一切。”[30]
写作目的
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内容充分表明了其写作目的。写这封信是为了记录写信人的反应并满足收信人的需要。
这封信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记录写信人听到好消息时的喜乐,这好消息就是收信人面临患难时仍能坚定不移。正如第1章所表达的,这消息使写信人着实为读者向神生发一种感恩之情。
这封信的另一个目的就是驳斥一些针对宣教士们所虚构的指控与恶意的中伤,因为当时这些言论正在帖撒罗尼迦流传。这些诽谤行动的主要目标是保罗,它显然是犹太人挑动的,目的就是离间这些归信者和宣教士们的关系。帖撒罗尼迦人若听信了这些指控,在马其顿的福音工作将受到致命的打击,因此必须驳斥它们。但保罗对它们的回答(包含在第2章和第3章里)并不是出自受挫的个人骄傲,而是护卫归信者信仰的强烈关切之心。
这些诽谤者所做的是人身攻击,其目的是通过败坏传信息之人的名声而打击帖撒罗尼迦人的信心,他们的新信仰是从传信息的人那里领受的。宣教士们是帖撒罗尼迦人所认识的第一批基督徒,这些信徒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基督徒生活和品格的本质。因此,如果敌人能够动摇归信者对这些使者的信赖,以致怀疑他们的道德操守和可信度,那么这些新信徒的信仰就会被有效地摧毁。
诽谤者的攻击针对的是宣教士们在帖撒罗尼迦开展工作的动机。他们企图将宣教士们与当时那些四处游荡、唯利是图的宗教教师归于一类,这些人不遗余力地向轻信的人们施展他们的伎俩,为的就是赚取个人的利益。当保罗还在帖撒罗尼迦时,那些在腓立比的“上当者”曾两次送钱给他,这岂不是充分地表明他的传道只不过是一个赚钱的手段吗?那些人的花言巧语、表面上关怀跟从者的动人演说,难道不都是他们寻求自我好处的幌子吗?
对于这些利己主义的毁谤性指控,保罗回击的方式就是提醒那些收信人回想他们与宣教士们交往的过程,因为对事实清晰的数算自然可以驳倒这些指控(2:1-12)。
这些诽谤者更进一步地指责保罗是一个怯懦的人,因为他匆匆离开了帖撒罗尼迦,并且一直没有再回去。当有人在地方官面前指控他散布有煽动性的教导时,他却没有勇气面对他们;当他的教导引发了危险时,他为了自保很快逃之夭夭,却留下他的归信者承受苦果。如果他真的像自己所说的那样关心他们,他为什么不回来呢?
为了驳斥这些指控,保罗表达了他对帖撒罗尼迦人强烈的向往,以及他多次为了回去见他们所做的努力,只是这些努力都遇到了阻碍。保罗甘愿舍弃提摩太对自己的帮助而将他差派回帖撒罗尼迦,这就证明自己是真心关怀他们,并渴望与他们重新建立联系。提摩太的任务一方面是要增进收信人属灵的益处,另一方面则是让保罗那急切关怀他们的心得到安慰(2:17-3:5)。
这些对保罗品格的恶意诽谤,就像将火把抛向一个不为人知的人,反而照亮了这位基督的使者正直、崇高的品格。
这封信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满足教会一些具体的需要,这些需要是提摩太汇报的。教会存在一些弊端和问题亟待解决。若是之前保罗能亲自回去,他一定已经处理好这些问题了。既然不能亲自回去,他就需要以写信的方式来处理。最后两章就是为处理这些问题而写的。
基于提摩太的报告,保罗认为有必要提醒这些帖撒罗尼迦的新信徒们,基督教的道德观远远地超越了异教的一切,借此保守他们远离先前异教信仰的恶毒影响。他还劝勉他们要继续彼此相爱并且诚实地工作(4:1-12)。他同时也解释了主为属他之人再来时要发生的事情(4:13-18),借此使那些丧失挚爱的人们得到安慰和坚固。他劝导每个信徒都要警醒谨守,因为主再来的时间没有人知道(5:1-6)。他呼吁他们要敬重那在他们当中做带领人的,要同心合意地确保教会所需的秩序和纪律,并要过圣洁的生活(5:12-22)。保罗这样的答复和教导,进一步证明了他真诚无私地关心收信人的属灵益处。
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写作地点和时间
写作地点
我们从使徒行传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帖撒罗尼迦前书是在第二次宣教之旅中写的。写作地点基本可以确定为哥林多。西拉是保罗那段旅程的同工,但他们在哥林多的工作结束后,使徒行传就没有再提及西拉了。保罗在雅典时差派提摩太回到帖撒罗尼迦(帖前3:1-2),这封书信就是在他从帖撒罗尼迦返回时写的(3:6-7)。从使徒行传18:1、5我们了解到,西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返回后,在哥林多与保罗再次汇合。这是在保罗离开雅典来到哥林多不久之后发生的,距保罗离开帖撒罗尼迦的时间最多不过几个月。因为他们三人当时都在哥林多,就此确证了写作的地点。
有一些抄本附有“写于雅典”的脚注。这脚注显然不是原文的一部分,它体现的是抄写员对写作地点的推论。这推论明显是不对的。它明显来自于对保罗“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3:1)这句话的误解。保罗这句话说的是一个过去的事件,“从而间接地暗示使徒在写这封信时已经不在雅典了”。[31]
写作时间
保罗的生平事迹,能够精准地推论年代的为数不多。但是他在哥林多的工作就是其中之一,因为它与世俗历史的年代表有交集,这交集就是它与迦流做方伯的时间部分重叠(徒18:12)。方伯的任期一般为一年,很少为两年。
20世纪,人们在德尔斐(Delphi)发现了一个保存得并不完好的铭文,内容是革老丢皇帝写的一封信,信中称迦流为方伯。革老丢将写信的日期记为“在他当权的第十二年,第二十六次被拥戴为皇帝”。[32]他当权的第十二年就是从公元52年1月25日到公元53年1月24日,而他第二十七次被拥戴为皇帝的时间在公元52年8月1日以前。因此,这个铭文明确地将迦流在哥林多的时间锁定在公元52年1月25日到8月1日之间。
但迦流是在那年的什么时候就任的呢?通常认为他抵达哥林多的时间是7月1日前后。这残缺不全的铭文显然表明迦流已经在位有一段时间,足以给皇帝提供一些关于德尔斐人的重要信息。由此得出的自然结论就是:迦流一定是在公元51年的仲夏时节在哥林多就任方伯的。这个日期是当今广为认可的。[33]
然而,其他一些学者坚称这个日期早了大约一年。伦斯基指出,“皇帝的命令为接受任命的方伯离开罗马去往就任省份指定了时间,这时间是4月1日,之后是4月15日”。[34]因此他认为,迦流并非公元51年仲夏就任,而是公元52年5月1日就任。哈罗普(J. H. Harrop)说:“几乎可以肯定,他做亚该亚方伯的时间是公元52-53年。”[35]这个观点将迦流来到哥林多的时间推后了十个月左右。
使徒行传的记载没有指明保罗被哥林多的犹太人拖到迦流面前是什么时候,但看起来明显是在迦流抵达之后不久。犹太人当然迫切地想要保罗尽早闭嘴。保罗跟迦流碰面的时间应当是在公元51年7月或是52年5月。
迦流来到哥林多时保罗在那里已经多久,这无法确定,学者们有不同的估计。伦斯基认为保罗在那里已经有六个月,[36]库梅尔(Kümmel)则说“保罗已经在哥林多一年半了”。[37]很明显,保罗在那之前已经在哥林多做了有力的事工,但路加指出,在那次遭遇之后保罗又在那里“住了多日”,这就说明那不是他在哥林多长达十八个月的事工的尾声(徒18:11)。看起来最可能的是:那时他们已经在哥林多一年左右。因此,保罗抵达哥林多的时间是公元50年仲夏或是公元51年初夏。
因为哥林多前书是在保罗到达哥林多不久后写成的,所以它的写作时间就可以确定为公元50年或51年的夏末秋初时节。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看到,这封信的写作距离基督钉十架的时间不超过20或21年,并且它看起来是保罗书信中最早的一封。
我们无法得知是谁将此信带到帖撒罗尼迦,但可以肯定他是一位私人信使。奥古斯都皇帝当时已经建立了一个帝国邮政系统,但那严格地仅限于国家官方通信。一般的信件仍需由专门的信使、朋友或过路旅客来送达。保罗通常派他的一位同工送信。鉴于他的信件的性质,让一个理解并支持保罗工作的人来传递更为合宜。
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真实性
帖撒罗尼迦前书是由保罗所写,这已经不再遇到严重的挑战。但是一百年前,许多学者对于它的真实性多有质疑,这主要是受到图宾根学派(Tübingen School)的影响。它的领袖人物鲍尔(F. C. Baur)只接受保罗为四封“主要书信”(Hauptbriefe,即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书)的作者,而否认他撰写了其余的保罗书信。范·曼恩(Willem Christiaan Van Manen)所代表的激进荷兰学派更是一概否认所有的保罗书信,认为没有一封是使徒保罗写的。
那些反对帖撒罗尼迦前书真实性的观点都不足取信、毫无凭证,这是今天公认的,事实上那些论点反而更能支持它的真实性。那些反对观点“完全为书信整体的语气与格调所抵消”。[38]假如以一个不带任何偏见的观点来读这封信,其所显示的真实性绝对不是任何仿造者所能模拟的。假如它是伪造的,那么对于此信的出现,目前还没有人能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前面所讨论过的历史背景,为保罗亲笔写此信的动机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它的词汇、风格、内容都有着真实的保罗特色。另外,正如库梅尔所指出的,“后来的作者在仿冒保罗写作时绝不会提到那没能实现的期望,就是能活着见到基督再临(4:15、17)”。[39]因此,安德烈·罗伯特(André Robert)和安德烈·弗耶(André Feuillet)明确地断言:“关于帖撒罗尼迦前书真实性的争论已经不复存在,因为现在的评论者都接受它是保罗的作品。”[40]
标题的解释
此信的标题显然不是保罗写的。它是抄写经卷的人加上去的,合适地指明这篇文献的性质、作者和目的地。
抄写员添加标题明显是便宜之举。通常一个抄写着该信内容的蒲草纸书卷,会有一个类似这样的标题写在卷好的书卷外面,以兹辨认。当保罗的书信被收集在一起时,这样的辨识标题就自然地会写在每封信的首端,好与其他书信区分开来。
在最古老的抄本当中,保罗书信的标题都是简明扼要的,因此这封信就被简要地称为“给帖撒罗尼迦人·一”(Pros Thessalonkeis A)。但后期的抄写员不满意这样简单的标题,于是他们通常会做扩充,除了收信人之外,他们又加上作者的名字(“保罗”,或有时为“使徒保罗”),还注明所写内容是一份“书信”。因为还有第二封写给帖撒罗尼迦人的信,所以这封信自然地被标定为“第一封”。
称这卷书为书信,准确地指明了它的性质。希腊文单词epistolē的意思是“由信使送达的”,就是一个“信息”,英文术语epistle就是由它衍生出来的;它还可以指一种书面通信,对象可以是一个人或一群人。该词在新约中共出现24次,可以被翻译为“书信”(epistle)或“信”(letter)。[41]这个术语所指的通信既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私人的。所有现存的保罗书信都是保罗以使徒的正式角色所写的通信。
有些作者坚称在信和书信之间有一个严格的区分,并称保罗所写的应当叫做信,而不是书信。阿道夫·戴斯曼(Adolf Deissmann)将信定义为写给特定的个人或群体的私人通信,而将书信定义为一种非个人的通用文学作品,其对象是普遍大众。[42]如果这样定义,那么保罗的作品无疑都是信。很明显,保罗并不是打着给特定群体写信的幌子,实际上却是给各地的基督徒写神学论文。保罗的所有作品都体现出亲密的、有感而发的特性,这是真正的信所具有的特征。他的作品都是由某个特定的生活境况而引发,目的是满足某个特定的需求。
但对于保罗的作品,我们不能过于明确地划分信与书信的界限。尽管这些作品明显表现出真实信件的特征,但是它们所包含的文学要素远远超出了普通的信所受的时间和地点的局限。他的信固然是写来满足当时读者的需要,但在神主权的安排之下,保罗及其他新约书信作者的作品对普世教会都具有恒久的价值与权柄。保罗的作品既然有这样的特性,我们不需要对既称它们为信又称它们为书信的惯例提出任何异议。
保罗的书信与当时的普通信件有着永远无法跨越的差异。那时代的世俗通信是由日常生活的琐事所引发,也随着时间逐渐被人遗忘;但这些信历经了这么多个世纪后,却仍保持着它们的重要性和价值。它们持久的重要性、属灵的活力以及翻转人心的大能永远标志着这些书信是独特的。因此莫尔(Moule)说:“之前从未出现过基督教书信这样的文献——保罗书信更是空前绝后。”[43]神的默示赋予保罗书信生命的活力,因此我们对它的学习也将会丰富多彩,满有收获。
[1]Edgar J. Goodspee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p. 4.
[2]J. B. Lightfoot, Biblical Essays, p. 254.
[3]同上,p. 255。
[4]Everett F. Harriso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p. 245.
[5] Lightfoot, pp. 257–58.
[6]James Hope Moulton and George Milligan, The Vocabulary of the Greek Testament, p. 525; Lightfoot, p. 256.
[7]Moulton and Milligan, and the references there cited; F. F. Bruce,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pp. 326–27.
[8]Roland Allen, Missionary Methods, St. Paul’s or Ours?, p. 12.
[9]Theodor Zah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1:203.
[10]R. C. H. Lenski, The Interpretation of St. Paul’s Epistles to the Colossians, to the Thessalonians, to Timothy, to Titus, and to Philemon, p. 286.
[11]Allen, p. 22.
[12]Bruce, The Books and the Parchments, pp. 139–40.
[13]William Mordaunt Furneaux,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p. 275.
[14]Donald Guthrie, New Testament Introduction, The Pauline Epistles, p. 179.
[15]同上,p. 212。
[16]James Everett Frame, A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Epistles of St. Paul to the Thessalonians, The International Critical Commentary, p. 7.
[17]E. J. Bicknell, The First and Second Epistles to the Thessalonians, Westminster Commentaries, p. xiii.
[18]Lenski,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p. 688.
[19]Richard Belward Rackham,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Westminster Commentaries, p. 296.
[20]F. W. Beare, “Thessalonians, First Letter to the,” in The Interpreter’s Dictionary of the Bible, 4:622.
[22]P. J. Gloag, “I Thessalonians,” in The Pulpit Commentary, p. v.
[23]Frame, p. 121.
[24] W. M. Ramsay, St. Paul the Traveller and the Roman Citizen, p. 228.
Moffatt Moffatt, James. The New Testament, A New Translation.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Hodder & Stoughton, n.d.
[25]James Moffatt, “The First and Second Epistles of Paul the Apostle to the Thessalonians,” in The Expositor’s Greek Testament, 4:3.
[26]Ramsay, p. 230.
[27]同上,p. 231。
[28]Chalmer E. Faw, “On the Writing of First Thessalonians,”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71:217–25.
[29]Ibid., p. 231.
[30]William Hendriksen, Exposition of I and II Thessalonians, New Testament Commentary, p. 13.
[31]Gloag, p. viii.
[32]关于铭文上的文字及讨论,见F. J. Foakes-Jackson and Kirsopp Lake, eds., The Beginnings of Christianity, 5:460–64; C. K. Barrett, The New Testament Background: Selected Documents, pp. 48–49; Adolf Deissmann, Paul, A Study in Soci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appendix 1 and plate 1; Jack Finegan, Handbook of Biblical Chronology, pp. 316–22; Finegan, Light from the Ancient Past, p. 282
[33]Finegan, Light from the Ancient Past, p. 282; Bruce,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p. 346; Werner Keller, The Bible as History, p. 386; Merrill F. Unger, Archaeology and the New Testament, p. 245.
[34]Lenski, The Interpretation of St. Paul’s Epistles, p. 215.
[35] J. H. Harrop, “Gallio,” in The New Bible Dictionary, p. 451.
[36]Lenski, The Interpretation of St. Paul’s Epistles, p. 215.
[37]Werner Georg Kümmel,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p. 180.
[38]Milligan, St. Paul’s Epistles to the Thessalonians, p. lxxv.
[39]Kümmel, p. 185.
[40]A. Robert and A. Feuillet,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p. 390.
[41]英王钦定本将epistolē一词九次译为“信”(letter),十五次译为“书信”(epistle);美国标准译本七次将其译为“信”,十七次译为“书信”。修订标准译本、新美国标准圣经和新国际译本则是通篇将其译为“信”。
[42] Adolf Deissmann, Bible Studies, pp. 3–12, 42–49; Light from the Ancient East, pp. 217–34.
[43]C. F. D. Moule, The Epistles of Paul the Apostle to the Colossians and to Philemon, Cambridge Greek Testament Commentary, p. 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