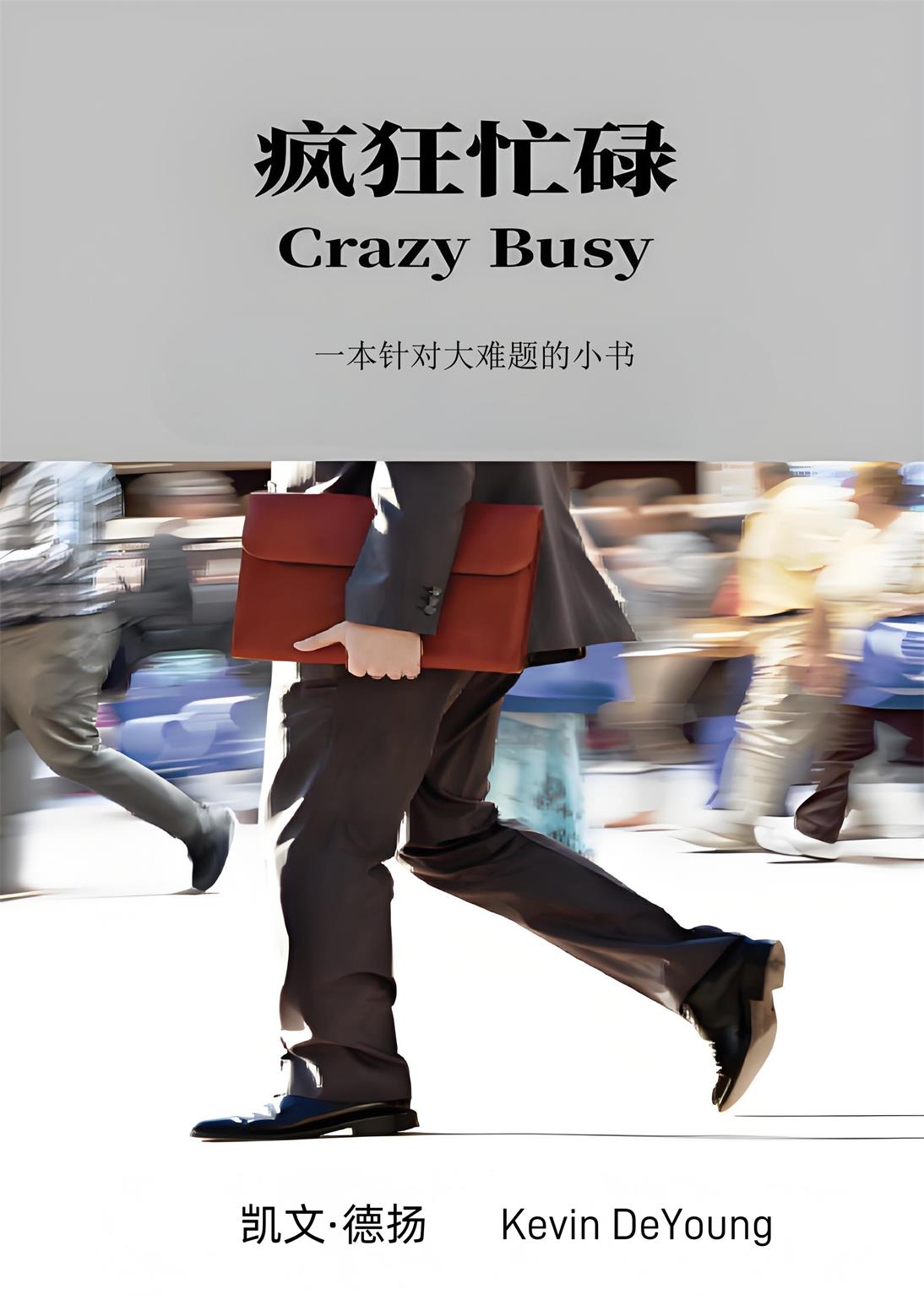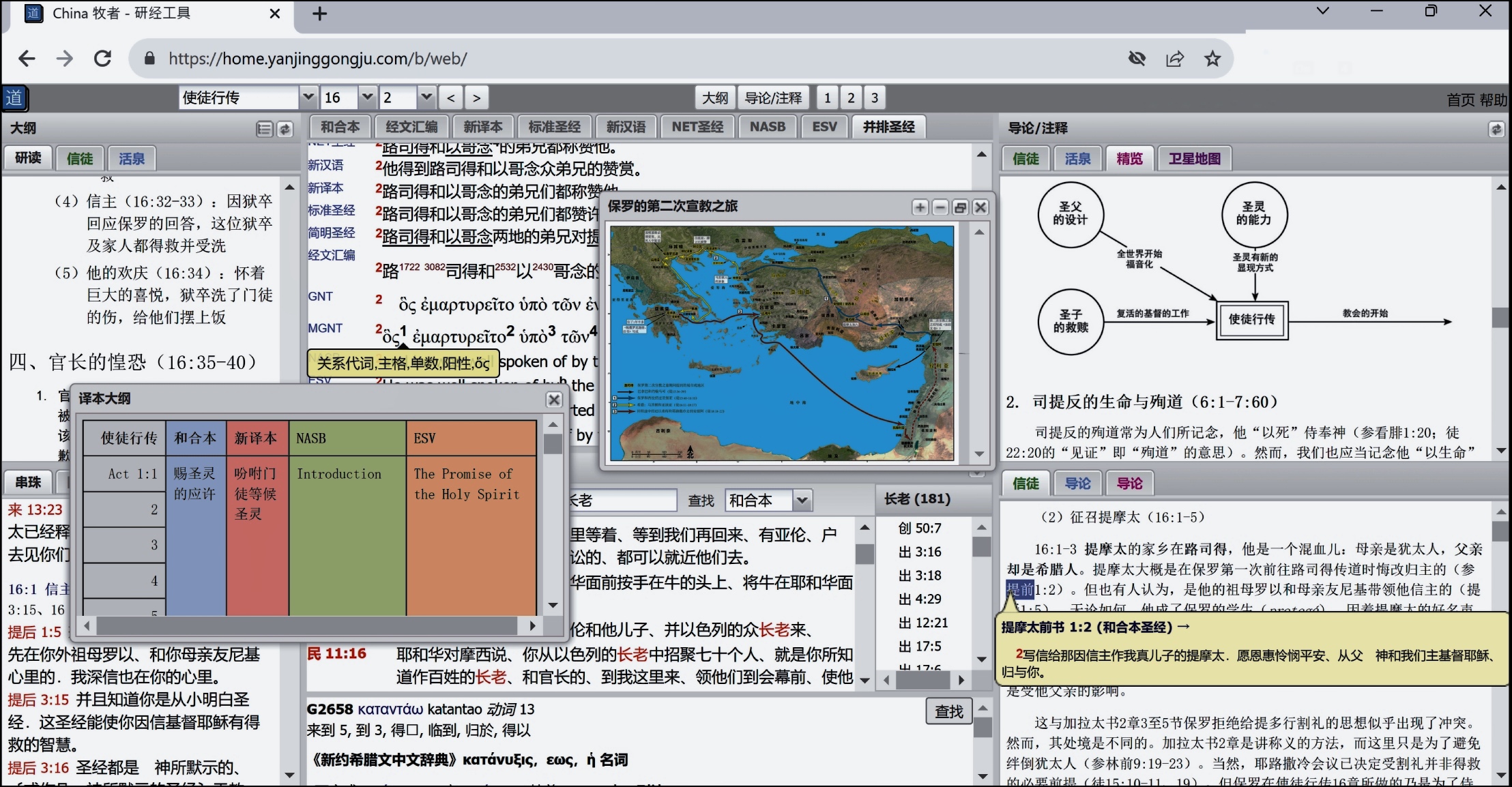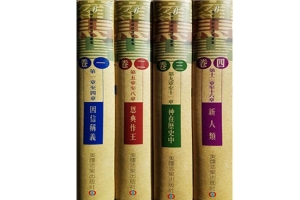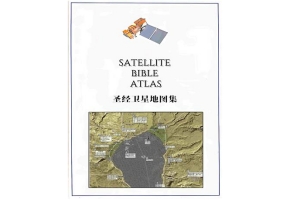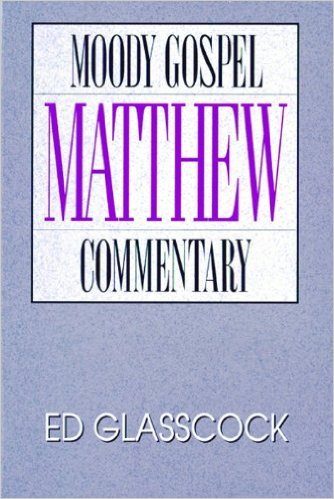第七章 深入思考
诊断5:你正在让屏幕扼杀你的灵魂
我在与几位受训参与服侍的学生交谈时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这问题的严重程度。当时,我正在我们一所顶尖的神学院演讲,课后两个人私下来找我,要问一个问题。他们小声说话,不敢和我直视,我凭这一点知道,他们有一些尴尬的话要说。我确定他们会讲和色情有关的事。果然,他们想谈他们在上网方面的挣扎。但让他们上瘾的并不是色情,而是社交媒体。他们告诉我,他们不能停止上脸书网(Facebook),花好几个小时时间浏览博客,漫无目的地上网冲浪。这是几年前发生的事,当时我不知道如何帮助他们。我之前还没有遇到过这种挣扎,我自己也没有沉迷其中。五年之后我遇到了这种挣扎,而且我沉迷其中。
我过去经常取笑写博客的人,我经常讽刺脸书,我经常取笑推特。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早早接受新科技的人。我从来不关心乔布斯准备要干什么。我通常对科技狂人翻翻白眼表示不屑一顾,直到我成为其中一员。现在我有一个博客、一个脸书页面、一个推特账号、一副蓝牙耳机、一部iPhone、一台iPad、家庭和办公室wifi、有线电视、一台Wii、一部蓝光播放器、多个电邮账号,以及不限流量的短信。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
我生于1977年,所以我仍然能记得数字革命之前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上大学的时候,我们需要去电脑实验室才能上网,而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电子邮件里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在网上也看不到任何有趣的事情。但是到我在神学院学习的时候,事情已经发生改变。电子邮件成了一种至关重要的沟通方式,互联网是我的朋友和我获取新闻(还有打梦幻足球游戏)的方式。但即使在那时候(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生活并没有如此互联。我在神学院学习期间才在房间里连接上了互联网——那种笨重、发出咔咔噪音拨号上网的怪物。我在上高中、大学和研究生的时候都没有手机。就在四五年前,我还不会用手机做什么事情,几乎不在家里上网。我并不是说那些日子更纯洁、更高尚,但我觉得我的生活没有如此碎片化,也没有太大压力。
棘手的话题是谈论科技
写科技方面的内容充满了挑战。首先,一些人根本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他们也许年纪较大,并不理解那些东西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吸引力。对这样的人,我要说愿主祝福你们,我希望你们就像我们过去那样享受真实的世界。
另一个挑战,就是我现在讲的一些细节很快就会在几年内不再适用,而那之后的几年里,所有这些都会过时。例如,大学生几乎不再写电子邮件,这让我抓狂不已。你需要在脸书上给他们发信息或留言,他们才会留意你。
写科技方面内容的第三个难处,就是人会有过度反应的倾向。在基督徒中,反科技进步的冲动非常强烈,人很容易认为,解决科技负荷过重的最佳办法,就是狂怒地反对机器。但是,对一个不会再回来的世界恋恋不舍,这并没有什么好处,那世界很有可能不像我们记忆中的那样美好。我喜欢把圣经放在我的手机上,把全国的街道地图放在我口袋里,可以随时查体育比赛分数,能整天和朋友联系,能在工作时发短信给妻子。毫无疑问,因着我们与所有事情相连,一些事情变得更好了。
问题在于有些事情并没有变得更好。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点,就是随着数字设备的存在和数字依赖程度的加深,新的能力和新的危险也随之而来。问题并不在于数字革命是否加深了我们生活疯狂的忙碌,也不在于它是否给我们的灵魂和理智带来了威胁。问题是,这些威胁是什么,我们如何面对这些威胁。
这些威胁是什么?
人们已经写了许多文章,还会继续写大量文章,来论述这无休止的上网欲望带来的危险。至于谷歌是否让我们变得愚蠢,以及年轻人是否要比从前更多或更少重视人际关系,我还是留给其他人去判断吧。现在我简单提出三方面,说明数字革命是让我们经历疯狂忙碌的帮凶。因为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些威胁,可能就有希望找到向前的出路。
第一,上瘾的威胁
这可能听起来过分言重,但事情就是如此。你能整天不看Facebook吗?你能一个下午不看你的手机吗?你能两天不查电子邮件吗?即使某人保证不会有紧急情况,也不会有新的工作任务,我们仍然很难离开屏幕。实情就是,我们当中许多人不能不点击鼠标。我们不能走开,即使几个小时也不能,更不用说几天或几周了。
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在他的畅销书《肤浅》(Shallows)中反思了他对互联网态度的改变。在2005年——他所说的“互联网进入Web 2.0时代”的那一年——他发现数字体验令他兴奋。他喜欢博客废掉传统出版工具的方式,他喜欢互联网的速度、便利、超链接、搜索引擎、音频、视频和每一样事情。但他回忆说,那时,“一条怀疑的蛇溜进了我的信息乐园。”[1]他意识到互联网已经控制了他的生活,而这是他的传统电脑做不到的。他的习惯正在改变,逐渐适应数字化的生活方式,他开始依赖互联网获取信息和开展活动。他发现他的注意力在衰退,“一开始我觉得这是中年思维呆滞的症状。但我认识到,我的大脑不仅仅精神恍惚,而且饥饿,它要求按互联网喂食的方式来喂它——它接受的喂食越多,就越饥饿。甚至我离开电脑时都渴望查电子邮件,点击链接,进行一些谷歌搜索。我要保持连接。”[2]
我已经留意到,过去几年里同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似乎工作不到十五分钟就有冲动要查电邮,浏览博客,或者看看推特上的更新,这是一种糟糕的感受。卡尔在《肤浅》的后记中解释说,他的书出版后,他收到一些人的反馈(通常是通过电子邮件),他们想讲自己的故事,讲述互联网是如何“分散了他们的专注力,使他们的记忆枯竭,或者把他们变成对“信息零食”上瘾的人”。一位大四学生给他发来一份很长的文章,描写了他从三年级以来是如何在一种“介乎中等到严重程度的互联网成瘾症”中挣扎。这位学生写道:“我不能深入或细致关注任何事物。我的大脑唯一能做的事情,确实也是它唯一想做的,就是重新回到那让人分心的、疯狂的网上信息闪电战中。”他承认了这一点,虽然他确信,“我生活中最幸福、最满足的时光,都与长期远离互联网有关。[3]”我们许多人——一小时接一小时,一天接一天——完全被上网的冲动胜过。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人被谁制伏,就是谁的奴仆”(彼后2:19)。
第二,麻痹(Acedia)的威胁
“麻痹”大概等于“懒散”或“无精打采”。它并不是休闲甚至懒惰的同义词。麻痹有冷漠和灵性疏忽的意味。它就像是心灵的黑夜,只是更无聊、更平淡、更无趣。正如理查德·约翰·纽浩斯(Richard John Neuhaus)所解释的那样,“麻痹是指被电视消磨的无数夜晚,这些夜晚既不是用于娱乐也不是学习,而是对抗时间和责任的麻醉式防御。最要紧的,麻痹是无动于衷,拒绝与其他人生命中的情感,以及神在其他人生命中的情感有所联系。”[4]
对于我们当中太多人来说,电子活动的忙碌和喧嚣是一种更深层次的麻痹的悲哀表达。我们觉得忙碌,却不是因为一种爱好、休闲或玩耍而忙碌。我们因为忙碌而忙碌,我们不是想办法利用我们空余的几分钟和几小时的时间,而是满足于在肤浅中畅泳,为打发时间而消磨时间。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对我们这时代的麻痹太习以为常,感受到这种忙碌加死寂的奇怪组合?我们总是滑动手指参与各样活动,却很少用心思考。我们不断下载信息,但很少能进入我们内心的深处。这就是麻痹——伪装成不断躁动的毫无目的。
第三,永远不孤独的危险,所有这一切都直接导致我们数字世界的第三种威胁。
我说“永远不孤独”,讲的并不是“老大哥”(Big Brother)在监视我们,或者安全受到入侵的危险。我讲的是我们不愿感到孤独的渴望。彼得·克里夫特(Peter Kreeft)说得对:“我们想要我们的生活变得复杂。我们无需如此,但我们想要。我们要苦恼、要纠结、要忙碌。不知不觉中,我们要的正是我们抱怨的事。如果我们闲暇,我们就会审视自己,倾听我们内心的声音,我们看到内心那极大的空洞,就感到惧怕,因为这空洞如此之大,只有神才能将它填满。”[5]
有时我在想,我如此忙碌,是不是因为我终于相信这谎言,就是“忙碌才是重点”。没有什么能让你如此忙碌——一直,随时随地面对任何人——就像把整个世界装在你口袋里那小小的黑色长方体里一样。在《哈姆雷特的黑莓手机》(Hamlet’s Blackberry)中,威廉·鲍尔斯(William Powers)把我们的数字时代比作一个巨大的房间,这房间中有十几亿人。但这房间虽然如此之大,每一个人都和其他人密切接触。随时都会有人过来拍拍你的肩膀——一条手机短信、一次点赞、一条评论、一条推文、一篇帖子、一条私信、一个新话题。有些人前来谈生意,有些人抱怨,有些人讲秘密的事,有些人调情,有些人向你推销,有些人给你信息,有些人只是来告诉你他们在想什么或做什么。这些昼夜无休止地进行。鲍尔斯把它称为是“一场不停歇的人类互动盛宴”。[6]
我们非常享受这房间——但这只不过是一阵子。最终我们对这不断的噪音感到厌倦。我们努力寻找一个个人空间。我们吃饭、睡觉、约会的时候,都有人来轻拍我们一下。甚至我们在卫生间也会有人拍我们一下,真是够了。所以我们下定主意休假,只是短短的假期。但似乎没有人知道出口在哪里,似乎没有人有兴趣离开。事实上,他们似乎都对你不想留下而感到不快。就算你找到了出口,通过这开口看到那迷人的世界,你都不确定在另一面的生活会是什么样。跳出去看看会发生什么,这是一次信心的飞跃。
鲍尔斯这比喻的重点应当是不言而喻的。就像托尔金的指环一样,我们既喜爱也厌恶这房间。我们想享受数字独立的无干扰空间,但这房间越发成为我们知道的唯一天地。其他人都留在房间里,我们怎么能走出去呢?没有了那无休止的拍打、拍打、拍打,我们怎么打发时间,让我们有事情可想呢?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互联网就像老鹰乐队(The Eagles)的《加州旅馆》(Hotel California)这首歌:我们想什么时候结束都可以,但我们永远都无法摆脱。
最可怕的部分就是我们可能并不想离开。我们有没有可能宁愿要那无休止的噪音,也不要那震耳欲聋的寂静?我们有没有可能并不在乎要听到神那微小的声音?有没有可能我们每天的琐碎和分心的事并不是由忙碌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或者根本没有强加在我们身上?有没有可能我们选择忙碌,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活在琐碎和分心当中?如果“数字忙碌是深入的死敌”,[7]那么只要我们绝不独处,我们就注定会陷在肤浅当中。我们的数字时代赋予了帕斯卡那句名言新的现实意义,“我经常说,人不幸福的唯一原因是他不知道如何安静地呆在他的房间里。”[8]
或者视情况而定,也可以选择不呆在房间。
我们能做什么?
那么现在怎么办?如果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这些就是我们面对的危险,我们该如何回应?我们能做什么?在此我提出几个观点,有些主要是实用方面的,有些则更明确地是神学方面的。
培养对科技和“进步”持有一种健康的怀疑态度
我已经说过,科技在许多方面改善了我们的生活,所以我并不是建议要放弃任何有开/关键的物件(虽然这可能会让你所乘航班的空乘人员感到高兴)。但是,我们可以与科技保持一点“距离”,更多意识到在最新创新之前这世上已有生活,没有创新也可以过得很好。尼尔·蒲思曼(Neil Postman)的告诫很有智慧:技术“绝不可被当作是事物自然秩序的一部分”。我们必须认识到,“每一项科技——从IQ测试到汽车,从电视机到电脑——都是特定经济和政治背景下的产物,伴随它而来的是一项计划,一项议程和一种哲学理念,它们可能会提升生活,也可能不会,因此要求仔细察验、批判和控制。”[9]
在与其他人联系时要更加深思熟虑和更多理解他人
不久之前,我留意到我一位朋友,在发了一封非常简洁的电子邮件之后,他在邮件末尾附上了一个关于“电子邮件约法三章”的链接。我有好几个礼拜都忽略了这链接(我太忙了),但最终好奇心胜过了我,我点击了那链接。让我感到吃惊的是,这份“约法三章”对减少花在电子邮件上的时间提出了非常有帮助的建议:不要问开放式问题,不要发没有实质性信息的回复,没有充分理由不要抄送给其他人,不要期望即时回复。让我惊奇的是这就是我不耐烦的样子——如果我给某人发短信,我期望在几秒钟之内得到回复;如果发电子邮件,我可能会允许等上几个小时,但对于给朋友的电子邮件,我期望在几分钟之内能收到回复。减少我们的忙碌,这是一个群体项目。我们必须承认慢回复和简短回复并不粗鲁。你不要指望每一次轻点按键,对方都必须立即回应。
刻意使用“旧”科技
如果你不想依赖你的数字设备,就要努力摆脱这些设备生活:读一本实体书,用纸写一封信,买一支很好的笔,打电话给某人,查字典,开车的时候关掉收音机、拔掉iPod插头,出去跑步时不听音乐,进实体店购物。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做一个怪人,而是重新学习一些做法,用“旧式”的方式来享受生活。
划定界限,并竭尽全力保护这些界限
摆脱屏幕控制最简单的方法,也是最难的步骤:我们不能一直都保持连接。我们不能再把电话带到床上了。我们不能在做礼拜时刷脸书,我们不能每顿饭都发短信。去年我妻子和我发生了一次最严重的争吵,因为她严厉指责我在吃晚饭时发推文。她如此严厉是对的,我答应她以后绝不会在吃晚饭时发推文(这承诺我想我已经守住了)。
大多数家庭可以用一个很大的篮子,把所有的手机、平板和笔记本电脑放在里面,让它们每天休息几个小时(吃晚饭的时候?灵修的时候?睡觉的时候?爸爸回家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都迫切需要“屏幕安息日”——一天中的某些时候(甚至一整天),我们不会“上网”或面对电子设备。如果我们不把看手机当作每天做的最后也是第一件事,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就会发现新的自由。在所有导致我忙碌的坏习惯当中,睡前查邮件和一醒来就查邮件的习惯可能是最糟糕的。
用我们的基督教神学来解决这数字时代的危险
虽然常识性的建议总是受欢迎的,但我们最深刻的问题只能由最深刻的真理加以解决。因着创造的教义,我们必须肯定人造的物品可以是促使人类兴旺和荣耀神的工具。因此,我们不能对新科技不屑一顾。但因为我们有一位神,他在永恒的过去拣选我们,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我们就不会迷恋最新的潮流和趋势。因着道成肉身,我们认识到在有形的地方与有形的人居住在一起是无可替代的。所以,我们不会接受虚拟的邂逅来替代血肉关系。
同样,因为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价值是有神形象的人,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我们就不会通过互联网来证明我们是重要的、有价值的和蒙爱的人。因为我们接受有内心的罪的存在,对我们在网上可能会屈服于潜在的偶像崇拜和试探,我们就不会视而不见。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堕落的受造之人,就会接受我们人类光景的有限。我们不能与成千上万的人建立有意义的关系。我们不能真正知道在这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我们不能同时既身在这里也身处那里。我们这数字时代最大的欺骗可能就是这谎言,这谎言说我们可以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我们无法做到这些事的任何一件。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缺席、无能和无知——并且是明智地作出选择。我们越早接受这种有限,我们就能越早获得自由。
[1]Nicholas Carr, The Shallows: What the Internet Is Doing to Our Brains (New York: Norton, 2011), 15.
[2]同上,16页。
[3]引自同上,226页。
[4]Richard John Neuhaus, Freedom for Ministry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79), 227.
[5]Peter Kreeft, Christianity for Modern Pagans: Pascal’s Pensées Edited, Outlined, and Explained (San Francisco: Ignatius Press, 1993), 168.
[6]William Powers, Hamlet’s Blackberry: A Practical Philosophy for Building a Good Life in theDigital Age (New York: Harper, 2010), xii.
[7]同上,17页。
[8]Blaise Pascal,Pensées, trans. A. J. Krailsheimer (New York: Penguin, 1966, rev. ed. 1995), 37.
[9]Neil Postman, 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New York: Vintage, 1993),184–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