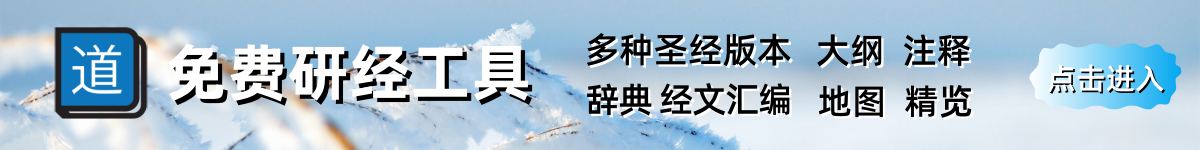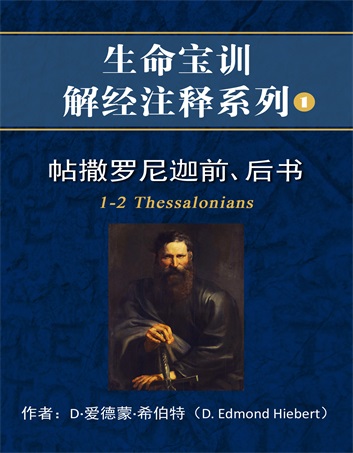导 论
与新约中其他的“后书”一样,帖撒罗尼迦后书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后叙。由于这两封书信的重点皆是基督的再来,在保罗的著作中它们被称为名副其实的末世论书信。因此,帖撒罗尼迦后书中所有信息的核心便是有关基督再来的真理。
一、这卷书的真实性
在早期教会中,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真实性似乎无庸置疑。该书信出现在保罗最早的书信清单里,流传至今。亨肖(Henshaw)对该书信的诸多外部证据作了下列的总结:“很显然,这封书信被波利卡普(Polycarp,又译作“坡旅甲”)、伊格纳修(Ignatius)以及殉道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所熟知,并且被收录在马西昂的正典(Marcion’s Canon)和《穆拉多利残卷》(Muratorian Fragment)中”。德尔图良(Tertullian,又译作“特土良”)、亚历山大的克莱门(Clement of Alexandria,又译作“革利免”)和爱任纽(Irenaeus)的著作都有直接引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经句。[1]米利根(Milligan)总结道,“与帖撒罗尼迦前书相比,后书的外在证据的日期更早,且更充分。”[2]
对于帖撒罗尼迦后书作者是保罗的抨击始于19世纪初。这些抨击的疑点完全是出于帖撒罗尼迦后书的内部因素,可笼统的归纳为下列两点。
1. 末世论的内容
第一类的抨击是针对这封书信中有关末世论的内容。这类抨击指出,由于保罗从未在其他的书信中提到过“大罪人”(the man of sin),所以他不可能在有关末世的经节中对这位人物作出如此详尽的描述。诚然,保罗没有在其他地方提到过这位重要的人物,但他没有在别处提及该人物并不代表在必要时他不能这样做。保罗对帖撒罗尼迦人说,当与他们同在一处时他曾和他们谈到过这些事(帖后2:5)。当然,我们不能认为保罗所描绘的景象与旧约相关的预言不一致,并且以保罗的孜孜以求和敏锐的头脑,他必定会借用旧约的预言来作为其论述的基础。
另一些人则认为,因为“大罪人”(the man of sin)这个人物的依据是尼禄复活传说(Nero Redivivus myth),因此这部分的内容必定是在保罗之后的时代里撰写的。该神话称,这位臭名昭著的皇帝并没有死,他在等待适当的时机回到这个世界,好将灾难带给他的仇敌及这个世界。但是近代的研究表明,这部分内容的撰写日期不可能早于1世纪80年代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保罗对该人物的描绘显然不是来自尼禄复活传说,而是当时有关敌基督的教导,其渊源远在保罗之前。米利根很正确地评论道,此类教导“早在基督教时代之前就已牢牢地生根在犹太历史中”[3]。因此,保罗所描绘的乃是基于旧约中的预言。
还有人说,由于帖撒罗尼迦后书对末世的教导与帖撒罗尼迦前书有抵触,所以保罗不可能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作者。帖撒罗尼迦前书对基督再来的描述是迫在眉睫且是骤然发生的;而帖撒罗尼迦后书却说基督再来之前会有一定的征兆。今天,如此的非议在神学界中已经无足轻重,因为在末世文献中,末世发生的骤然性与其前兆经常同时出现。威肯豪泽(Wikenhauser)指出:“甚至在耶稣对末世的教导中,我们也发现了基督再临前的征兆(可13:6及以下),以及警告人要警醒,因为那日子是不确定的(可13:33及以下)。[4]
今天,即使批判学者也承认,在末世教导上的差异不足以否定保罗是这两封书信的作者。有人认为这说明了“同一作者可持有多种迷乱的末世观”[5]。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仅仅说明保罗是一位明智且实际的人,在环境的压力下,他可以自由地改变自己的论点。[6]
那些对圣经默示论视为权威看法的保守派学者认为,没必要去做这样的解释。他们的看法是,这两封书信的本身都是正确无误的。斯克罗吉(Scroggie)认为,当人们认定被提和显现是基督再来的两个不同阶段,那么两封书信之间所谓末世教导上的差异自然就化解了。[7]就连那些对基督再来没有做任何阶段划分的学者,都坚持两封书信之间并无任何真正的不一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中,主的再来被描述为突然的、犹如贼一般;而帖撒罗尼迦后书则强调主的日子尚未来到,来临之前必然会有征兆。但是,这些征兆并不足以准确地告知主再来的日子,因此人们还是会为它的突然临到而感到惊讶。
现今,从本书信的末世特征进行的论证已经被认为不足取信。雷克(Lake)提到近代的研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已经“果断地把末世的论点从对帖撒罗尼迦后书真实性的质疑清单中除名了”[8]。
2. 文学关系
第二类的抨击是针对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真实性,此攻击是基于这两封书信的文学关系。
有人说这两封书信有太多共同点,令人难以相信保罗会写两封相似的书信给同一个教会。该论点认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以保罗这样一位头脑清晰又富有创意的人,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写出如此相似的两封信给同样一群人;并且认为这两封书信的共同点更像是在暗示帖撒罗尼迦后书是由一位聪明的模仿者所写。虽然两封书信之间有惊人的相似点,但是没有必要去夸大其实际的相似性。[9]两封书信之间的相似之处总计还不到整封书信内容的三分之一,而且这些在语言上的实际相似之处通常并不是出现在相应的章节中,而是从两封书信整体内容中抽取出来的。
当一位作者在短时间内处于类似的情境下写信给同一个教会时,若认为他不可以借用他先前书信的内容,这种观点当然是非常武断的。扎恩(Zahn)认为,保罗在写帖撒罗尼迦后书之前先念过前书的初稿,因此两封书信才会有这些相似之处。[10]如果书写该书信的原因是帖撒罗尼迦教会对前书的一些内容产生了误解,这就更能理解了。假如帖撒罗尼迦后书真是由一位模仿者所写,很难理解这位模仿者为何不更多地引用帖撒罗尼迦前书,以及他为何把自己局限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而不去借用保罗其他书信的内容。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有人称两封书信的语气存在差异,表明这两封书信的作者不是同一个人。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作者对他的读者和蔼热诚、极富情感;相比之下,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作者则较为冷淡且正式。但是,这些所谓的缺乏亲切感只局限于某些短语(帖后1:3,2:13),并且只是表面印象而已。弗雷姆(Frame)指出,帖撒罗尼迦前书所表达的热诚和亲密与作者极力地为自己辩护有关,他继续评论道,“若将作者的自我辩护略过,这两封书信在语气上的差异便不那么明显了。”[11]批判学者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看到的较为冷淡和正式的语气,很自然地被理解是因为当时状况有改变,导致作者心情上的改变。从帖撒罗尼迦教会传来不良变化的消息,自然会导致回信时更加克制与冷静的语气。
德国批判学者威尔德(Wrede)在他的著作Die Echtheit des zweiten Thessalonicherbriefs(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真实性)一书中声称,这两封书信的内容使人无法接受它们是由同一位作者写给同一间教会的。他坚持认为,帖撒罗尼迦前书暗示着其读者纯粹是外邦人,而帖撒罗尼迦后书则带有强烈的犹太色彩,并假定其读者比外邦基督徒对旧约有更多的认识。他总结道,帖撒罗尼迦前书是写给一间外邦教会,而帖撒罗尼迦后书则是写给一间犹太教会,因此这两封书信不可能都是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因此,我们必须否定保罗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作者。
这样的结论是无法立足的。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中,并无任何内容是外邦信徒所无法了解的。当一个外邦信徒成为保罗所教导的教会成员时,他们会跟随保罗的带领接受旧约的权威性,并借着七十士译本很快地去了解旧约内容。在使徒行传(徒17:1-4)里记载了帖撒罗尼迦教会成立时,旧约在保罗的教导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鉴于马可福音中有关末世教导(可13章)毫无疑问是写给外邦信徒的,因此我们不能说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末世教导对当时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外邦信徒而言是晦涩难懂的。此外当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时,外邦信徒也从他的讲道中对这样的教导有所了解(帖后2:5)。
那些否定帖撒罗尼迦后书真实性的学者无法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来说明该书信是如何被教会毫不犹豫地接受为真迹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帖撒罗尼迦教会在收到一封保罗亲笔的信函之后,会如此轻易地将一封伪信当成保罗的真迹。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一位模仿者不可能写出如此具有保罗特征的书信。古德斯皮德(Goodspeed,又译作“顾斯庇”)的结论是,这封信“具有太多的保罗书信特征,言辞犀利,因此不应将其视为赝品”[12]。
学者们普遍认为,甚至自由派的学者们也承认,这些批判的攻击并没有动摇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真实性。因此,一位非保守派学者——莫法特(Moffatt)——评论道:
“公平地讲,几乎每一处似乎呈现出有异于保罗书信特征的地方,无需牵强地利用任何证据,都可以根据保罗本人写了这封书信的假设得到解释(大多数近代的编辑者都如此认同。)[13]
历经一个半世纪的批判研讨后,学术界再次达成共识,支持传统基督教的论点,确认保罗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作者。
二、两封书信的关系
即使在那些拥护帖撒罗尼迦后书真实性的学者中,也有人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两封书之信间关系的问题上采取了与传统观点对立的看法。其中,有两种观点须要一些探讨。
1. 分裂的教会
哈纳克(Harnack)对威尔德的看法多加赞同,为要证实保罗是帖撒罗尼迦后书作者的身份,他做了如此的臆测,“除了帖撒罗尼迦前书所针对的外邦信徒之外,当时还有一个成立较早且为数较少的犹太群体,帖撒罗尼迦后书的对象就是这一群人。”[14]他认为,帖撒罗尼迦教会中的不同群体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27就曾暗示过,保罗要求“要把这信念给众弟兄听”,好像除了收到这封书信的这群人之外,还有另一群人的存在。为了巩固自己的立场,他还引用了帖撒罗尼迦后书2:13很有问题的翻译:“他拣选了你们为初结的果子”(译注:和合本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这句话显然不能运用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外邦信徒身上,因为他们不是马其顿的第一批信徒,但是这句话确实指向了犹太信徒,因为他们是那省第一批归主的犹太人。
但是,如此解读当时的情形是极不合理的。格思里(Guthrie)正确地指出,“像保罗这样一位倡导合一的人,是极不可能分别写信给同一间教会的两个对立群体,为教会的不和推波助澜。”[15]他因哥林多教会内部的不和所作的强烈谴责,让人无法想象他会纵容帖撒罗尼迦教会内部的不和。帖撒罗尼迦教会内部存在这样的不和,与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14所写的内容不一致,即他把犹太地的教会作为帖撒罗尼迦教会中外邦信徒的榜样。
在两封书信开篇的问安中,抬头是完全一致的,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这两封书信的收信人是同一群人。哈纳克推断说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抬头原是“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那受过割礼的”,最后六个字是后来才被删掉的。这种牵强的说法,凸显他理论上的漏洞。
2. 撰写的顺序
根据两封书信的名称,一般认为帖撒罗尼迦前书写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之前。但是,有些学者认为两封书信的撰写顺序应该是相反的。曼森(Manson)并不同意哈纳克对两封书信之收信人的推论,他认为可以透过颠倒两封书信的顺序来看这一问题。他坚持认为,颠倒书信的顺序可以消除对帖撒罗尼迦后书真实性的所有质疑,并可免除它被批判成“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惨澹附笔”[16]。有一系列的论点支持这种颠倒书信顺序的说法。
根据帖撒罗尼迦后书的记载,教会正在所遭受迫害(帖后1:4-7),而帖撒罗尼迦前书却将它看作是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帖前1:6,2:14-15,3:2-4)。但是,这样的观察并不能就此下结论说,在撰写帖撒罗尼迦前书时教会所遭受的迫害已经完全成为历史。在帖撒罗尼迦前书3:4中,保罗警告读者们迫害随时可能来到。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中,有关迫害的经文皆出现在保罗对过去的追忆中,因此他很自然地以过去式来描述。
有人认为,帖撒罗尼迦后书3:17提到的签名说明此信是他的真迹,“若不是在第一封书信中,就毫无意义”[17]。但是保罗并没有在他所有的“前书”中留下可识别其真迹的表达。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中,保罗对于提摩太所带回的消息喜乐洋溢,说明当时并不需要提防冒名写信这类事。但是,当保罗在撰写帖撒罗尼迦后书时,就很有必要提醒教会提防那些谎称出自他手的假冒书信(帖后2:2)。
有人坚持认为,帖撒罗尼迦后书处理的内部问题是“作者刚刚听到的新情况”,而“帖撒罗尼迦前书所提及的乃是大家都熟知之事”[18]。因此,帖撒罗尼迦前书4:10-12需要透过帖撒罗尼迦后书3:6-15才能理解。但是,我们也可以合理地去理解,帖撒罗尼迦前书中对那些爱管闲事之人的柔声劝阻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因此帖撒罗尼迦后书需要用较强烈的口气来处置。假如帖撒罗尼迦后书对如何处置那些闹事者的指令在先,我们很理解为何帖撒罗尼迦前书却完全没有提到这些蓄意违反指令的人。
如果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成书时间更晚,并且是在帖撒罗尼迦教会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那么信中提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些成员去世的事才更容易理解。但是,只因为有一些成员去世,并不能代表这须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当然,三两个信徒的去世就能引发帖撒罗尼迦前书所处理的问题。从宣教士离开帖撒罗尼迦到提摩太从那里带回消息,其间有够长的时间发生这些问题。
有人声称,如果帖撒罗尼迦后书的顺序在前,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中所指“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的这句话才有意义。但是,鉴于他们之前在此事上接受过精确的口传教导,这句话在第一封书信里也同样合理。
有人觉得,若帖撒罗尼迦前书成书在先,而前书5:12-13中所隐含的领袖结构的建立则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是,帖撒罗尼迦前书所隐含的领袖结构并不复杂,不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形成。按惯例,一旦教会成立,保罗便会督促他们指派长老(参 徒14:23)。
有人认为,“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教会看起来比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教会更为成熟。”[19]因此,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7里,保罗提醒会众要效法他及其同工们;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1:6-10中,会众不但效法了保罗等人,并已经成为他人的榜样。但是,这两处所提到效法的重点很不一样,无法就此论定帖撒罗尼迦前书里会众的灵命更为成熟。帖撒罗尼迦前书所指的是信徒的归信,而帖撒罗尼迦后书则要求得救后的信徒过一种平稳且有秩序的生活。
有人认为,由于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篇幅较短,理当在前;而帖撒罗尼迦前书其实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的补充,因为“它的内容更充实,并引进了许多新的内容,例如第五章出现许多谜样的禁令。”[20]但是,我们没有正当理由指定前书一定要比后书短,同时也无法证明帖撒罗尼迦前书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的附录。当两封书信都谈到同一个题材时,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篇幅通常要长于帖撒罗尼迦前书。
曼森认为,有关于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19、13,5:1中反复出现的“论到”一词,是指帖撒罗尼迦人在写给保罗的回信中所提出的进一步的问题,因为帖撒罗尼迦后书没能回答他们所有的问题。[21]但是,这种说法并不能使人信服,无法证明保罗是在回复帖撒罗尼迦教会写给他的信。保罗重复地使用“论到”一词,可以合理地被理解为他是针对提摩太口传报导中所提的问题在作解答。
这种颠倒正典顺序的作法产生了许多问题。因此,为了对事件重新排序,曼森推测提摩太是带着帖撒罗尼迦后书从雅典被差派去帖撒罗尼迦(帖前3:1-5)。提摩太被差派回到帖撒罗尼迦的原因,正是为了更多了解当时教会的状况。因此,根据曼森的假想,我们很难理解在保罗还没有收到提摩太的消息之前,他却能如此笃定地写出教会的状况。此外,如果帖撒罗尼迦后书确实撰写在先,很难理解保罗为何在前书中没有提到这封信,来表达他对帖撒罗尼迦会众的深切挂念。
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中,保罗并没有表达任何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所展现出来的亲切思念,以及急欲回到帖撒罗尼迦的心意。既然帖撒罗尼迦后书没有表达这种向往,就不能合宜地将其放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之前。比较好的解释是保罗当时在哥林多时写了这封信,那时他得知主的旨意是不让他回到帖撒罗尼迦(徒18:9-11)。
另外,帖撒罗尼迦后书似乎提到了之前的一封信(帖后2:2、15,3:17)。假如帖撒罗尼迦后书确实撰写在前,那我们必须假定另一封信现在遗失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并没有任何先前通信的暗示,因此,在传统上所认可的顺序是更合理的。
为了支持传统的顺序,亨德里克森(Hendriksen)指出,帖撒罗尼迦前书所强调的是保罗与此信读者的亲身交往,当时这经历才发生不久、仍历历在目。帖撒罗尼迦后书则提到写给他们的一封信。第一封信记录了那些读者如何因信接受了福音,而在第二封信中,保罗则为他们的信心在成长表达感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传授给读者们有关“被提”(帖前4:13-18)的重要教导;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帖后2:1)中,保罗则提到之前他们已接受过这方面的教导。[22]
按照传统的顺序,两封书信内容的发展更具逻辑性。因此,尼尔(Neil)评论道:
两封书信所处理的每一个主题,即迫害、主的再来、懒散,其困难程度有明显的加剧,再加上帖撒罗尼迦前书所描写当时状况的发展,要改变两封书信的顺序便更无从谈起了。[23]
我们的结论是,没有任何证据可颠覆这两封书信正典上的顺序。自从2世纪以来,这就被教会接受为自然的顺序。
三、写作地点和时间
1. 写作地点
当保罗写这封信时,西拉、提摩太是和他在一起的(帖后1:1)。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是保罗最初在哥林多传道时写的,[24]显而易见,不久之后这封信也是在那里写的。支持这个论点的事实是,保罗离开哥林多后,这三个人在新约中就再没有一起出现过。事实上,麦克尼尔(McNeile)以“无有”为据来理论,暗示他们三个人很可能确实在以弗所一起同工过(徒19:1-20),此信就是在那里写的。[25]但是,由于两封书信密切的关联,是不太可能在时间上有如此大的间隔。
2. 写作时间
帖撒罗尼迦后书撰写的时间因两封信之间所假设的间隔而定。学者们对这个间隔的分歧极大,短至数日[26],长达一整年[27],但是这两种观点似乎都很极端。一般广为接受两封书信撰写的间隔是二到三个月。因此,按照我们对帖撒罗尼迦前书日期的推断,帖撒罗尼迦后书撰写的日期应该是在公元50年或51年的秋天或是初冬。
四、写作情境和目的
1. 写作情境
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后书最直接的原因,是他收到了所爱的帖撒罗尼迦信徒近况的消息。这有可能是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信差在那里停留了足够长的时间,有机会观察到近况的发展,然后带回了这个消息。那时帖撒罗尼迦和哥林多两城有密切的商业往来,因此会有许多机会将不同的消息带给保罗。
帖撒罗尼迦信徒的消息是忧喜参半。让保罗欢喜的是,听到帖撒罗尼迦信徒在信心与爱心上的成长(帖后1:3),同时他们在逼迫患难中仍然坚定不移(帖后1:4)。
但是令人担忧的是,一些关于“主的日子”的极端理念已经在教会一部分人的心中生根,这种理念使他们既惊慌又兴奋,显然给他们的日常生活都带来了不良的影响。有些信徒被转变中的基督徒生命体验冲昏了头脑,认为新时代(主的日子)已经到来,弥赛亚随时会公开显现(帖后2:1-3)。正是针对这些状况,保罗才撰写了这第二封书信。
2. 写作目的
这封书信反应出从帖撒罗尼迦所带来的正负两面的消息。保罗借这机会称赞那些信徒在信心与爱心上的成长(帖后1:3),同时也勉励他们在迫害中要坚定不移,因为当主再来审判时,必会为他们所遭受的迫害还他们一个公道(帖后1:5-12)。
但是,撰写此书信的真正动机是要纠正有关“主的日子”教义上的错误教导,同时斥责一些信徒不按规矩而行的行为。在第2章里,保罗纠正他们认为“主的日子已经来临”(威廉姆斯译本Williams)的错误观念;然后在第3章中,强烈地谴责那些不按规矩而行的错误行为。在这两封书信中,保罗并没有指出这两个问题的因果关系。虽然有些解经学者否定两者间的任何明确关联,[28]普遍认为有关“主的日子”的教导会令人兴奋,因此自然会造成某些信徒的怠惰。这种关联表明,整封书信的教导都与基督的再来有关。
[1] T. Henshaw, New Testament Literature in the Light of Modern Scholarship, p. 228.
[2] George Milligan, St. Paul’s Epistles to the Thessalonians, p. lxxvi.
[3] 同上, p. lxxvii.
[4] Alfred Wikenhauser, New Testament Introduction, p. 369.
[5]在米利根第86页内被引用。
[6] Edgar J. Goodspee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p. 19.
[7] W. Graham Scroggie, Know Your Bible, vol. 2 of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Scriptures, The New Testament, p. 114.
[8] Kirsopp C. Lake, “The Authenticity of 2 Thessalonians,” in Contemporary Thinking About Paul. An Anthology, comp. Thomas S. Kepler, p. 235.
[9]对比帖后1:3与帖前1:2;帖后1:5与帖前2:12;帖后1:7与帖前3:13;帖后2:16-17与帖前3:11-13;帖后3:8与帖前2:9;帖后3:16与帖前5:23;帖后3:18与帖前5:28。
[10] Theodor Zah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1:250.
[11] James Everett Frame, A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Epistles of St. Paul to the Thessalonians, International Critical Commentary, p. 35.
[12] Edgar J. Goodspee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Testament, p. 21.
[13] James Moffat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iterature of the New Testament, p. 79.
[14] Kirsopp C. Lake, “The Authenticity of 2 Thessalonians,” in Contemporary Thinking About Paul. An Anthology, comp. Thomas S. Kepler, p. 237.
[15] Donald Guthrie, New Testament Introduction, The Pauline Epistles, pp. 189–90.
[16] T. W. Manson, Studies in the Gospels and Epistles, p. 267; see also Johannes Weiss, The History of Primitive Christianity, 1:289–91.
[17] T. W. Manson, Studies in the Gospels and Epistles, p. 267; see also Johannes Weiss, The History of Primitive Christianity, p. 273.
[18] 同上,272页。
[19] R. Gregson,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the Thessalonian Epistles,” The Evangelical Quarterly 38 (April–June 1966): 80.
[20] 同上,77页。
[21] Manson, pp. 274–77.
[22] William Hendriksen, Exposition of I and II Thessalonians, New Testament Commentary, pp. 16–17.
[23] William Neil, The Epistles of Paul to the Thessalonians, Moffatt New Testament Commentary, p. xx.
[24]参帖撒罗尼迦前书导论,地点与日期。
[25] A. H. McNeil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New Testament, p. 113.
[26]威肯豪泽(Wikenhauser)271页提到格拉芬(Graafen)。
[27] John Bird Sumner, A Practical Exposition of St. Paul’s Epistles to the Thessalonians, to Timothy, Titus, Pilemon, and to the Hebrews, p.73. (但是,他接受帖撒罗尼迦前、后两封书信是在哥林多撰写的论点。)另参Arno C. Gaebelein, The Annotated Bible, 4, section 1, p. 125。
[28] D. D. Wheldon, A Popular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4:404; Wilbur Fields, Thinking Through Thessalonians, Bible Study Textbook, p. 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