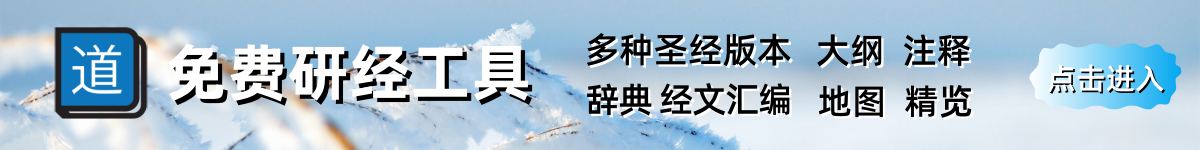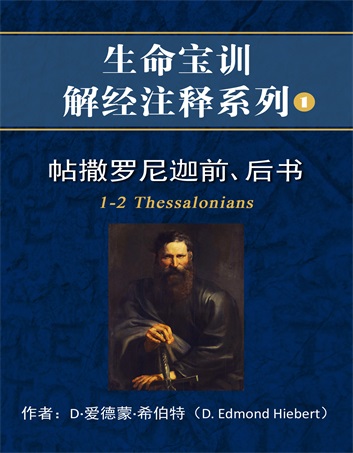六、结 语(3:16-18)
16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17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凡我的信都以此为记,我的笔迹就是这样。18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这个简短的结论可分为三部分:为读者们所献上最后的祈祷(16节),保罗的亲笔问安作为此书信真实性的标记(17节),以及结尾的祝福(18节)。
(一)结尾的祈祷(16节)
这封书信以作者们为读者们所作的第四个祈祷结尾(参1:11-12,2:16-17,3:5)。这些重复且自发的祈祷,显示出祈祷的真意以及保罗为人代祷的一贯风格。
这祈祷是由一个小品词de所引入,在此被翻译为“现在”(译注:新国际译本直译,和合本省略的)。这样的翻译赋予其过渡的意味,代表在此进入此信的结尾。埃利科特认为,这个词有些许的对立之意,“将先前的告诫与这祈祷稍作对比。”[1]这是作者们认识到的另一点,即若不是主在这些读者身上动工,他们的劝诫皆为枉然。因此,他们乐意地从谴责之心转变为祈祷之意。
“愿赐平安的主”指明了祈祷的对象。这个翻译成“他自己”的人称代词(autos,译注:按照原文语序位于句首)再次凸显在句首(参帖前3:11;帖后2:16),语意强烈。“愿他,那赐平安的主”将他们的思想从纠正不端行为所作的努力转向主,他的平安必须充满并掌管读者们的心。
他们所请求的对象被称为“赐平安的主”,这个称呼仅在此书信中出现。保罗在其他地方使用的是“赐平安的神”(罗15:33,16:20;林后13:11;腓4:9;帖前5:23)。这两种称呼似乎作同义词来使用。阿德尼(Adeney)认为,“在此,保罗似乎并没有对神与基督作任何的区分。”[2]虽然这不是有意要对神性作区分,[3]但这些书信中一致的使用方式强烈支持“主”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个属格名词“平安的”原文带有定冠词,即“那平安之主”,标志着他与圣徒之间的独特关系,他是基督徒平安的真正来源和赐予者。这平安是透过他在十字架上所作的工而建立(弗2:14-16),现在作为礼物赐给所有信徒(约14:27)。
所请求的是平安的主能“给你们平安”。在这句子中两次使用“平安”,强调祈祷的重心。所用的过去不定式祈愿语气表达了祷告的意愿,概要地陈述了这个求神赐读者们平安的请求。这种平安永远不能通过个人的努力获得,而必须以白白的礼物来接受。“平安”原文带有定冠词,就是“那平安”,指向那众所皆知的唯有耶稣基督才能赐给的平安。这平安是指客观的,是作为礼物接受的平安,但这平安不应该与信徒对平安的主观体验分开。他们所请求的并不是为了免受迫害,也不是为了止息教会内的纷乱,而是请求那些透过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工、与神和好的人,得到内在的平安与灵魂的喜乐。
后面的两个介词短语说明他们为读者们所祈求平安的全面性,那就是“随时随事”。第一个短语与时间长短有关,第二个则是指所经历的各种遭遇。“随时”(dia pantos),又作“经过所有的”或“不断的”,指出这平安会持续不断、连绵不绝地涌流出来。“随事”指的是在生命所经历的各种状况下仍持有这平安,新美国标准圣经译作“在各种际遇中”。不论生命的际遇多么令人烦恼,都不能夺取这内心深处的平安。
“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并不是另一个祈求,而是指为平安所做的祈祷被成就的方式。这平安并非遥不可及的礼物,而是靠着主亲自与他们同在而来,因为基督所赐的礼物不能与基督的位格分开。这请求神同在的祈祷乃是基于神自己的应许(太28:20)。
作者们很明确地祈求主的平安“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是指在帖撒罗尼迦的所有信徒,包括那些不按规矩而行的人。所有的人都包括在他们的善意与祈祷中。他们都需要主耶稣基督亲自“与”(meta)他们同在所带来的平安,并能实际体验到在他们中间有主的同在。主常与他的子民同在,但他们不见得每时每刻都能意识到他同在的事实。在这节经文中“所有”共出现过三次(希腊词为每一个。译者注:新国际译本直译,和合本分别作‘随’时‘随’事,‘众’人),凸显出“神的作为涵盖一切。”[4]
(二)保罗的亲笔问安(17节)
这亲笔签名的问安明确地表明,保罗在此之前一直在口述这封书信,但是此刻他拿起了听写者手中的笔,亲自写下了结尾的问候语。这种撰写书信的方式是有迹可循的,有证据表明保罗有口述书信的习惯(罗16:22;林前16:21;西4:18)。许多学者认为,保罗在加拉太书6:11中的意思是说,他在那里才开始亲自写了书信剩下的部分。但是,由于保罗在写结束语的时候从未使用书信式的不定过去时时态来表达,因此学者们(如扎恩、伦斯基、维斯特〔Wuest〕等)认为,最好将加拉太书整封书信看作是保罗亲笔撰写的(参门19节)。
对于保罗口述书信的原因,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臆测。有人认为,他使用这种方式可能是因为他眼睛不好,或他不能快速地书写希腊字,或由于织帐棚维生使他的手指僵硬而无法书写,抑或他的手指在一次鞭打的过程中受伤等。这些臆测都不足取信,因为真正的原因在他的书信中并没有说明,但这种方式显然是非常方便的。当时,有能力的听写者比比皆是,多数的教会都可能有自己的专职抄写员,让保罗可以雇用。他们可能使用一种速记方式、轻易地抄下他的口述。[5]这种撰写方式使保罗从实际的繁琐写作中解脱出来,让他可以自由地专于思想的进展和精准的表达。
此处的译文“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与原文有出入。按原文的字序,保罗的名字出现在最后,“这问安乃是出于我自己的手,保罗的”(威廉姆斯译本)。他将自己的签名放在信尾是很罕见的,因为按照当时书信的格式,作者通常在书信的开头交代自己的名字。保罗在此特意标明这封书信乃直接来自他,他本人对此负责。在这两封给帖撒罗尼迦信徒的书信中,保罗提到西拉与提摩太为事工的伙伴,很显然他们也参与讨论过此书信的内容,但这封信最后还是由保罗口述,注明他是要为此书信负责的作者。
接下来,保罗马上附加上他亲笔签名的重要性:“凡我的信都以此为记,我的笔迹就是这样。”“以此”(ho)是中性,很明显不是指他的问安,而是指保罗亲自写信的这一事实。保罗的签名注明了此信是真迹,同时也让帖撒罗尼迦信徒知道,若没有他亲笔签名,没有任何文件可以声称拥有他的权柄。“凡我的信”并不代表有许多具有他亲笔签名的书信在流传。一般学者公认,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保罗最早撰写的书信。[6]保罗似乎有意要让他的签名来鉴定之后他所写给他们其他书信的真实性。显然地,保罗采取这种鉴定书信的方式,为的是阻止他人再借着一封冒名的信,持用他的权柄来提倡某一个神学论点(参2:2)。帖撒罗尼迦前书并没有提到他亲手写的问安,所以其中的问安很可能不是他亲笔写的。但在此之后,保罗与同工们发现有人用他未曾写过的文件,来冒用他的权柄,因此他开始以签名来验证自己的书信。
保罗在新约的书信中,只有其他两处提到过他的亲笔签名这一事实(林前16:21;西4:18)。至于有关所提“凡我的信”(译注:直译为“我所有的信”),这不必代表“仅限于他新约的书信,因他撰写过圣经之外的书信,这事也是广为人知的(参林前5:9)”[7]。虽然保罗在新约的其他书信中并没有再提到过亲笔签名这一事实,但并不能证明他没有坚持这一作法。在保罗原信件中,他的亲笔签名很容易从笔迹的差异上辨别,因此他不需要特别指明。德斯曼(Deissmann)复制了一份写于公元50年的具此风格的草纸书信。信的主体部分是一个笔迹,结尾的问安与日期记载却是另一个笔迹,很明显这是作者所写。德斯曼认为这非常明确的证据指出“我们不能认定,保罗只在特别注明是他亲自写完的信件中亲手写结尾部分。”[8]
“我的笔迹就是这样”似乎很明显的指出,保罗与听写者笔迹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这”(houtōs)意为“以此方式、如此”,为要突显他笔迹特有的风格,“这就是我的笔迹”(威廉姆斯译本)。至于他笔迹的特点是什么,并没有另加说明。加拉太书6:11曾提到他的手写字体特别的大而粗壮。贝利(Bailey)认为这粗壮的字体“可能是他刚劲直率风格的自然表达”。[9]但是,加拉太书所提到的大字体可能是用来强调的,其意代表他书写的方式,而不是所写的内容,似乎才是鉴定他真迹的标志。但是,也不要就此认为保罗发明了一种奇特而很难模仿的字体,来作为他的印记。吕内曼认为,这种错误的看法是“将现代的思维转嫁到古代”。[10]另有他者认为,能鉴定保罗真迹的标志乃是第18节中的问安方式。但这种可能性极小,因在保罗的书信中,他结尾的问安方式变化众多。假如此处所指的乃是某种问安方式,模仿者能轻易地采纳同样形式,因此无法确保其真实性。但是他笔迹的独特风格,却能成为可靠的鉴定依据。
(三)对全会众的祝福(18节)
这封书信与帖撒罗尼迦前书5:28以同样的祝福作结尾,只是就如第16节,在此多了“众人”一词。虽然宣教士们在信中认为必须用强烈的言词来遣责这些不按规矩而行之人,但是他们渴望表明对众人的亲切思念与祈祷的记念,同时也希望众人都能得到神的祝福。康斯特布尔(Constable)如此评论道,“众人”一词“听起来像是为教会的合一所作的最后呼吁,每人都需要服从保罗的教导与训诫来促进教会的合一。这种合一的心唯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才能得到”[11]。
有些抄本在此加了“阿们”一词。虽然这样的添加有不少抄本支持,但是现代的编者一致认为其渊源乃是抄写者的仪文。
有些手稿有脚注“撰写于雅典”,这显然是抄写者后加的注解,这体现出抄写的错误,其来由乃是基于对帖撒罗尼迦前书3:1的错误解译。就如帖撒罗尼迦前书一样,这卷书信乃是撰写于哥林多。
回顾这两封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书信,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其中不朽的真理对今日的信徒仍然是如此地适时。“基督死与复活二十年后,对于当时基督徒信仰和生命某些层面的印象,这两封书信带给我们的启发,在某种程度上令人颇感意外。”[12]我们再次被提醒,使徒时代的众教会并不完美,但是当那些成员与永活的基督相遇之后,他们的生命和思想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他们已经出死入生,他们活泼的信心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视他为救主与主宰,他们热切地盼望他的再来。但是,这种对未来的盼望,因他们还没有完全了解,以至于产生了一些反应,宣教士们认为有必要给予修正和引导。这种对末世观的担忧,使得保罗在这两封信中特意强调这盼望,因此这两封书信在保罗书信中被视为末世书信是合宜的。沙夫(Schaff)对保罗书信一般的论评也适用于这两封书信。
它们是一时的论谈,也是时时的论谈;它们是时代的产物,也是跨越时空的真理。除了四福音书之外,无论是“神为”还是“人为”,没有其他任何著作能将如此多的思想浓缩成如此精简的字句。它们所讨论的是可以挑战不朽思想的至高主题,而这一切都发生在由贫穷人、没有文化的工匠、自由民和奴隶构成的卑微的社会小群面前。然而,它们对教会具有更真实、更普遍的价值,远远超过从奥利金(Origen,又译“俄利根”)到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所累积的各种神学体系。[13]
或者,还可以加上巴特(Barth)或布尔特曼(Bultmann)。
[1] Charles J. Ellicott, A Critical and Grammatical Commentary on St. Paul’s Epistles to the Thessalonians, p. 141.
[2] Walter F. Adeney, Thessalonians and Galatians, The Century Bible, p. 255.
[3] “在某种层面上,那配得称颂的三一真神中的任何一位都可确实地被称为‘赐平安的神’。当我们思考他们的职掌功能时,可见到(a)父神是所有平安的源头(帖前5:23;腓5:7、9),(b)圣子就是我们的平安(弗2:14),(c)圣灵将这平安带给人(加5:22)。”G. W. Garrod, The Second Epistle to the Thessalonians, p. 145 (黑体字来自原著)。
[4] Ernest Best, A Commentary on the First and Second Epistles to the Thessalonians, Harper’s New Testament Commentaries, p. 346.
[5] “罗马帝国时代的生意人皆擅于写信。他们发明了三种不同的速记方式来帮助经营生意。”James C. Muir, How Firm a Foundation, p.14。
[6] 有些学者,如亨德里克森(Hendriksen),认为加拉太书的撰写日期要早于帖撒罗尼迦前后书。William Hendriksen, Exposition of Galatians, New Testament Commentary, pp. 14-16。
[7] Robert L. Thomas, “2 Thessalonians,” in The 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 11:337.
[8] Adolf Deissmann, Light from the Ancient East, p. 158. For the letter, see fig. 19 and pp. 157–59.
[9] John W. Bailey and James W. Clarke, “The First and Second Epistles to the Thessalonians,” in The Interpreter’s Bible, 11:338.
[10] Gottlieb Lüneman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Handbook to the Epistles of St. Paul to the Thessalonians, Meyer’s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p. 254.
[11] Thomas L. Constable, “2 Thessalonians,” in The New Bible Knowledge Commentary, New Testament, p. 725.
[12] F. F. Bruce, “Thessalonians, Epistles to the,” in The New Bible Dictionary, p. 1272.
[13] Philip Schaff,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1:741.